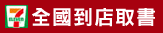紅葉階前——憶錢穆先生
世間之事,常有 迴路轉的奇妙現象。我在武大時,沒能趕上錢穆先生講學的盛況。沒想到在編譯館這位置上,卻因「武聖岳飛事件」,讓我有機會與錢穆先生聯繫上。 迴路轉的奇妙現象。我在武大時,沒能趕上錢穆先生講學的盛況。沒想到在編譯館這位置上,卻因「武聖岳飛事件」,讓我有機會與錢穆先生聯繫上。
在我進館之前,「大學叢書」收到一份台大歷史系林瑞翰教授的書稿,尚在審查階段,是否出版未定,卻有報紙報導:林瑞翰教授所著《中國通史》是台大一年級必修的中國通史課本,竟誣蔑岳飛跋扈,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十二道金牌才召得他回朝。宋高宗為什麼殺他,並不是那麼單純的事。如此不敬之言,台大竟作教材,而國立編譯館竟然接受林教授《宋史要略》書稿,將要出版,簡直是動搖國本!
有一位自稱是岳飛小同鄉的李某,連續寫了數篇,說:「你們侮辱武聖,就是數典忘祖!」還有一位罵得最凶的立法委員吳延環,不但以筆名「誓還」在《中央日報》專欄不停地討伐,並且在立法院正式提案,令教育部答詢。王天民館長雖在各報來訪時詳細說明:「館裡接受書稿,既尚未審查,更未有出版計畫。」但是各報繼續登載責罵的文章,有一則報導竟然說:「據聞該館負責此事者,係一女流之輩,亦非文史出身。」王館長是歷史教授出身,知道當時各校學者無人願審,亦無人能抵擋此政治意識的洶湧波濤,命我去拜見由香港來台灣定居的錢穆先生,請他作個仲裁,說幾句話,指引一下國立編譯館對此書處理的態度。
我對於前往錢府的事感到萬分躊躇,不願再遭遇坐與不坐、茶與不茶的場面。待我一向非常客氣的王館長說:「沒別的辦法,委屈你也得去一趟。」
錢先生來台灣居住的素書樓,位於台北士林外雙溪東吳大學後面一個小山坡上,有一條依坡而建的石階路。我去外雙溪的路上實在不知是何場面,深悔誤入宦途。車到外雙溪,沿東吳大學山徑到山坡盡處,按了門鈴,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階。錢先生出見時,尚未坐下便說,「我已在電話中說不能審查。」我困窘至極,囁嚅而言:「我剛由學校來國立編譯館三個月,這份書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輿論責難不止,請您看看,我們當如何解此僵局?」大約全出於同情心吧!錢先生接過書稿,放在几上。我道謝後倉皇辭出,幾乎是奔下石階,心想大約再也不用來了。
誰知三天後意外接到錢先生電話,說請林瑞翰教授去談一談。再過數日,林教授親自到館裡,他毛筆工整細密的手寫稿二十二頁,綜合加添了錢先生面談時給他的六種新資料,補充他書中岳飛部分。資料非常充實穩妥,提供了多面的論述。
但是仍救不了我們,教育部來了一道公函,轉來立法院的質詢提案,「國立編譯館擬靠錢穆先生的聲望,將詆毀武聖岳飛的作品,作大學用書出版,動搖國本……。」命令館長隨教育部長羅雲平去立法院說明。質詢之前數日,我帶了許多資料去立法院圖書館謁見吳延環委員,詳細說明《宋史要略》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無人肯審,更不會近期出版。質詢日,我坐在備詢官員最後一排硬椅子上,王館長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員席;他有多年教學經驗,對答時如在課堂,不慌不忙,質詢者雖然來勢洶洶,但亦不知應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學術著作如何「動搖國本」?我自大學時期在學潮中開始(直到今日台灣的選舉文宣)看盡了政治意識控制學術思想之猙獰面貌,沒想到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苦讀、進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資格,在大學教文學課程,竟到這裡來看著我的老師王館長被這些人指手頓足地以政治意識型態指責,如此傷尊嚴,多麼不值得!我心中充滿憤慨和悔憾,回到館裡,即寫辭呈,館長問我:「你覺得在這種局勢下辭職是保持尊嚴麼?你此時離開能說明什麼立場呢?」他從桌上拿給我一封剛收到的掛號信,是錢先生寄來的,退還我隨書稿送上的審查費兩千四百元,一紙便箋上寫:「無端捲入貴館書稿輿論漩渦,甚感煩惱。茲退回審查費,今後請勿再牽涉本人意見……。」館長說,這本書我們短期內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須去對錢先生致歉,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就這樣,我開始了登上素書樓石階十八年的緣份。轟轟烈烈的岳飛事件之後,是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部編本,再接著是高中中國文化史的新編,每件事都是新聞的焦點。在那一段時期,我身兼人文社會組和教科書組主任的雙重責任,隨時有去住保安大飯店(警備總部)的可能,幸好生長在我那樣的家庭,經歷過許多大風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說,你當了這麼芝麻大的官,卻惹上了天天上報的麻煩,必須記住蔣總統文告裡指示的,應當時時「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爸爸以前曾說:「我這個女兒膽子小,經常『處變大驚』。」想不到,一九七○年代的國立編譯館竟是我的「壯膽研究所」。
其實,輿論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間希望學術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數並不少,那時仍健在的陶百川、黃季陸、陳立夫、王世杰等長輩,也贊成國中與高中的國文教科書,以文學情操教育為主,少宣揚政治理念。至少,那時的教育部長羅雲平實際上是支持的。在陳述編書理想時,我終於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他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從那時起,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後來錢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潛老師的學生,談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樂山為武大講學之事。我告訴他,我聽學長們談到,清晨持火把去禮堂上他的課的情景。因此,有時錢先生也留我坐談當年事。沒有公事時,逢年過節和他壽誕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楓樹長得很高了。一九八五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楓葉。
那些年,錢先生的眼睛已漸漸不能看書了。和錢先生真正談得上話以後,雖然時時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嚴,也感到一種寬容和溫熙,也許我沒有歷史學問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麼是不能越過的界限。當他問我坊間有什麼新書時,我有時會以外文系的知識,冒冒失失、糊里糊塗地帶給他館裡出版的書,也買些坊間話題論著,如柏楊的書,送給他。
我回台大之後,也常與他談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書,譬如最早先用《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時學生的反應,談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尋》。對於追尋寂寞這種文化現象,錢先生感到相當「有趣」(他的無錫發音至今難忘)。其實,一九八三年他親自贈我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回憶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詳見第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