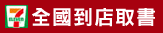台大外文系
由那幾步台階走下來,穿過如今已不存在的舟山路,進入台大舊牆內的校園,穿過校警室、福利社,從行政大樓和農化館間的小徑出來,立刻面對文學院的紅樓。橫切過種滿了杜鵑花樹的椰林大道和紀念傅斯年校長的傅鐘,即可從氣勢寬闊的門廊進入迴廊。對於我,似乎有一種「儀式」似的意義。這敞朗、陳舊的迴廊,以大半圓的弧形,穩坐在台北帝大(創立於昭和三年,1928年)初建的校園中心,兩端開著小小的門,中間包著一個小小的院子,和我三十年前初見時完全沒有改變。在台灣漫長的夏天,隱約可以感覺到迴旋的、流動的文學餘韻(whispering coolness),安頓我的身心。
很難與記憶妥協的是,外文系的辦公室,已經搬到樓下,現在是個熱鬧的地方了。進了院門樓下右轉一排大屋子,只有這一間的門經常開著,迎面是一座木櫃,上面放著一把當年標準辦公室用的大鋁茶壺,沒有力氣從木櫃上提下那把茶壺的時候,你就該退休了。茶葉裝在白色小麻袋裡,由總務處分發給各系辦公室。我至今記得咖啡般的茶色與苦澀的茶味,兩節課之間實在太渴,也常得去喝一大杯,茶幾乎永遠是冷的。木櫃有數十個格子,當作教師的信箱,後面桌椅相連,坐著五位助教和一位事務員,川流不息的人和事。一直到我退休,外文系沒有一間真正的教員休息室,上課前後的「交誼」似乎都在迴廊「舉行」。我至今記得,有時從「二十四教室」出來等下一節課鐘響,相當疲勞地靠窗台站著,會看到走廊那一端出現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友,免不了有「驚呼熱中腸」的場面,然後匆匆忙忙在粗糙的木窗檯上寫下電話號碼,各自奔往教室。
那時外文系編制已近八十人,還有許多位兼任老師。第一批開課的老師如英千里、王國華、黃瓊玖、蘇維熊、李本題、夏濟安、黎烈文、周學普、曹欽源、曾約農等都已離開。一九七○年以後的台大外文系,有人戲曰:「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在那陳舊斑駁但敞亮可愛的迴廊,來來去去的學生有許多年是聯考第一志願分發來的,心理上也許有置身雕欄玉砌之感。而課程確實有很「現代化」的大改變。最大的推動者,恰好一位姓朱,一位姓顏。朱立民和顏元叔先生在一九六○年代後期由美國拿到文學博士學位歸國,在台大校園被稱為「稀有貴重金屬」;不久另一位文學博士胡耀恆先生也回到台大,以最新方式講授西洋戲劇,帶領學生以比較文學方法關懷中國戲曲的發展。
影響最大的改革是重編大一英文課本,以增強全校學生的英文能力,擴展人文和科學方面的知識。為本系一年級學生開設「文學作品讀法」,列「中國文學史」為必修課,此課前後有臺靜農、葉慶炳、林文月、柯慶明等中文系名師授課,不僅使學生真正認識中國文學的傳統和演變,也增強中文和外文兩系的師生情誼,影響學生日後進修的視野,甚為深遠。
「英國文學史」改為兩年十二個學分的課程:第一年由中古英文時期(The Middle Ages,1485)到十八世紀(the Eighteenth Century);第二年由浪漫時期(The Romantic Period,1785-1830)到二十世紀(The Twentieth Century)。 使用的課本以重要作品為主,不僅是背景、潮流、發展的敘述而已。我教的時候已使用全世界的標準本,諾頓版的《英國文學史》(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共約五千多頁。
在台大我一直講授英國文學史第二年課程,有一年顏元叔先生出國,由我代課,上了英國文學史第一年課程。此課我在中興大學教過四年,有過相當研究。同一星期之內要按不同的進度調整自己的思緒,在二年級的教室講八世紀北海英雄史詩〈貝爾伍夫〉(Beowulf),甚至還須放一兩次古英文發音的唱片。第二天則在三年級班上費力地闡釋十八世紀奧秘浪漫詩人威廉.布雷克〈心靈旅者〉(William Blake,1757-1827,The Mental Traveler),此詩描寫兩個反方向轉動的循環,自然與人生,其中奧秘實非課堂中可以完全闡釋。我在中學時曾讀過一篇英國人寫的文章,他說人腦裡似有許多隔間(compartments)儲藏不同的知識。我在腦中清清楚楚區分英國文學史各階段重要作品,各自為它的時代璀璨發光,所以自己並沒有時空混淆或時代錯置(anachronism)之虞。
浪漫時期(The Romantic Period)
回到台大第一堂上課的情景,很難令人忘記,那該稱之為「盛況」吧!鐘響後,我走到迴廊左轉第一間「十六教室」,以為自己走錯了,除了講台,座位全部坐滿,後面站到貼牆,窗外也站滿了人!這門必修課全班有一百三十多個學生,而第十六教室只有五、六十個座位,所以引起那個盛況的場面。後來調整到新生大樓,第二年回到文學院一間大階梯教室。
我確實是在惶恐中走上講台,勉強平靜地說了開場白,迅速地抓住了唯一的救援,一支粉筆,寫了兩行這一年的計畫:起始於浪漫時期和將要講授的第一位詩人威廉•布雷克。為了穩定自己和「聽眾」,我先用中文說明英國文學史和一切文化史一樣,劃分時代和流派都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定名。如自一六六○年英王查理二世復位到桂冠詩人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1631-1700)的十七世紀後半期為「復辟時期」(The Restoration Period),和我們即將開始正確閱讀的浪漫時期,都有很複雜的歷史意義。我不贊成,也沒有能力用中文口譯原作,所以我將用英文講課,希望能保存原文內涵的思想特色。我不願用「浪漫時期」的中文譯名,簡稱那一個常以熱情進入深奧內在探索的時代。因為「Romantic」所代表的既非唯美,亦非中古以降羅曼史(Romance)中虛構的奇情。它是一種對崇高(sublime)理想永不妥協的追求。強調創造力與情感抒發的浪漫主義其實是對前世紀守教條的新古典主義的反動。其回歸自然(return to nature)的呼求,強調大自然引導個人心靈對真善美的追尋與沉思。
中國近代教育系統以英文為主要外國語以來,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以英國文學史為必修課,乃是必然的發展。至今最簡單明確的原因,仍可用泰恩(Hippolyte Taine,1828-1893)以德國人的觀點來說明,他寫《英國文學史》說,要藉一個豐富而且完整的文學成長史分析時代與種族的關係。在他之前,在他之後,西方文學理論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流派,忙煞學院中人,但泰恩的文學三要素——時代、民族、環境——仍是文學作品能否傳世,或隱或顯的基本要素。
教文學史並不是教文學欣賞,不能以個人的趣味選材。每個時代的精神與風格不是一時的風尚,而應存在於才華凝聚的長篇傑作,或是形成個人風格的一些連續短篇。
華茲華斯的《序曲》(Wordsworth, 1770-1850, The Prelude 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1798-1839) 是這位湖濱派(Lake School)詩人一生創作的最高成就。十四卷的長詩氣度恢宏,堪媲美彌爾頓史詩《失樂園》(John Milton, 1608-1674, Paradise Lost, 1667),記錄了詩人個人心靈的成長與自然的交會互動。
柯立芝的〈古舟子詠〉(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1797-1799) 則是浪漫主義宣言《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的第一首詩,以航海象徵人生的罪與罰,和求取救贖的神秘旅程。
拜倫(Lord Byron,1788-1824)的《唐裘安》(Don Juan)雖未完成,但仍是文學史上最長的諷刺詩。主人翁以西班牙到處留情的風流浪子為名,此詩註明Don Juan須以英文發音為唐裘安,而不讀作唐璜,被塑造為一個文質彬彬、魅力十足、在愛情上被動的年輕人。他不似拜倫筆下聲名狼藉的拜倫式英雄(Byronic Hero)那般憂鬱和孤傲,而是個勇敢、充滿巨大熱情、拒絕虛偽道德教條,為追求自由的英雄。第三章中對希臘璀燦文明走向敗落的悲嘆,常被政治革命者引用。
雪萊《解放普羅米修斯》(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Prometheus Unbound)是一齣四幕的抒情詩劇,取材自希臘神話,描寫普羅米修斯因向天神宙斯盜火給人類使用,被忿怒的宙斯用鐵鍊鎖在高加索的懸崖邊,陷入永無止盡的痛苦中也不妥協,直至迫害者因殘暴招致毀滅才得解放。在雪萊心中,心靈因有愛和寬恕而更顯崇高。
即使寫作生命只有五年的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他直至生命盡頭,仍放不下曾投注心力的史詩長篇《海柏里昂的殞落》(The Fall of Hyperion, 1819)。詩人藉夢境寫舊日神祇殞落的痛苦,抒寫自己對文學的追尋。他在夢中置身林中荒園,來到一個古老神廟,廟頂高入星空。站在廟旁大理石階前,他聽到馨香氤氳神殿中有聲音說:「你若不能登上此階,你那與塵土同源的肉身和骨骸,不久即將腐朽,消失湮滅於此」;他在寒意透骨浸心,死前一刻,奮力攀上第一階,頓時生命傾注於業已冰冷凍僵的雙足,他向上攀登,好似當年天使飛往天梯。神殿中的女神對他言道:「一般的人生都是苦樂參半,而你卻鍥而不捨,探索受苦的意義,你不就是夢想族(the dreamer tribe)嗎?要知道詩人與做夢者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撫慰世人,後者卻只對這個世界困惑。」詩人在夢境中承受女神給予重重的試煉,一如當初詩歌之神阿波羅歷經由死而生的震撼一般,不斷反覆問答思辨。詩人自覺似有神奇的洞視能力 (to see as a God sees), 得以深刻敏捷的洞察生命之理。年輕的濟慈受死亡陰影環繞之際,猶奮力創作,憑藉神話之世代更替自我期許,以更寬廣的視野與胸懷為詩歌辯護,流露詩人對文學永不熄滅的熱愛與追求。但在任何教室,只能以短詩入門,如:
濟慈不僅因閱讀喬治•查普曼新譯的史詩《伊利亞德》(George Chapman,1559-1634,Iliad),寫出了第一首傳世的《初讀查普曼譯荷馬史詩》(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也深受被後世稱為「詩人中的詩人」史賓塞《仙后》(Edmund Spenser,1552-1599,Faerie Queene),以及彌爾頓《失樂園》等巨著之啟發,而投入大量心思寫中長篇。他認為必須認真經營,給足夠的迴旋空間才能容得下泉源迸發的想像和豐沛的意象,所以他先寫長詩〈聖亞尼斯節前夕〉(The Eve of St. Agnes),再寫短詩〈無情的美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這些晶瑩璀璨的半敘事體詩,和他的頌詩一樣,是世世代代傳誦的珍品,可見他的詩並非只是依憑靈感之作。
(詳見第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