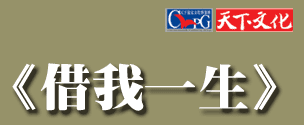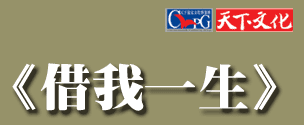五、
離開妻子家鄉後,我們到上海看望我的媽媽,並安排到慈溪老家為爸爸修墳的事。按照家鄉的風俗,我們早幾年已為爸爸、媽媽找好了墳地,還修了「生壙」,現在需要整修一下,待到冬至那天,將爸爸的骨灰盒捧回去,葬到那裡。
正忙著這些事,美國開始打伊拉克了。
世界文明廢墟中最讓我痛心的老傷疤,終於再度撕開。看著電視裡熟悉的原野、河岸和街道,我一下子從親情悲悼中拔身而出,日日夜夜地逼視著人類文明的大悲劇。
妻子指著電視畫面,追問著我們當初「集體失蹤」後的行經地,然後嘆息,三年前她一個人的喪魂落魄,怎麼一下子變成了全世界的驚心動魄。
由於怕在旅途中漏掉任何一條最新戰報,我們決定,等到戰爭告一段落再離開上海。誰知,戰塵未散,疫情大熾,SARS快速傳染,處處封鎖。這是我們近年來在上海停留最長的時日,還是因為災難。
爸爸一走,竟然讓我們遇到了大大小小那麼多事,因此只覺時間過得飛快。轉眼,是冬至了。
我和妻子提前一天回家鄉打點。第二天早上,幾個家人租了一輛旅行車,陪著媽媽,捧著爸爸的骨灰盒,也到了山口。我、妻子和一大批親眷、族人已在那裡等候。
等車一到,先把媽媽扶到她的表弟長標舅舅家休息,因為鄉俗不主張她出現在爸爸的下葬現場。
我從弟弟手中接過爸爸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琴花阿姨早已準備好一把大傘罩在我頭上。長標舅舅提醒我,要邊走邊喊。我問他喊什麼,他說,就喊「爸爸,回家了!」
於是我喊:「爸爸,回家了!我們回家了!」
我童年時非常熟悉的山草氣息撲面而來。眼前就是了,大地的祭壇,百家的祠堂,永遠的吳石嶺。
上山坡了。山坡邊上已排著親眷、鄰里送的一個個花圈。腳下是山石和泥沙,還有大量落葉和松針。我又喊:「爸爸您看,那麼多人陪著您,琴花阿姨給您打著傘,我們一起回家了!」
山坡下那條由東向西的路,就是我在六歲前的一個晚上獨自翻過吳石嶺和大廟嶺去尋找媽媽的路,這事,爸爸一直不知道。山坡上全是密密的楊梅樹,我在〈牌坊〉中寫過,小學同班同學中有一部分住在山腳下,家裡都有楊梅樹,楊梅季節邀請老師進山吃楊梅,老師進山後只聽到四周親熱的呼叫聲卻不見人影,呼叫聲來自於綠雲般的樹叢。這些描述,爸爸都讀過,他現在就要到綠雲深處長眠。
山坡往西一箭之遙,就是上林湖了。這裡細潔的泥土、清澈的湖水、純淨的炭火,燒製過曹操、王羲之、陶淵明、李白的酒杯。我在〈鄉關何處〉裡寫到過這一切,這篇文章爸爸也讀過,從今天開始,他要夜夜傾聽那遙遠的宴饗。
宴饗結束之時,爸爸也許能見到那位尚未確證的祖先余上林先生,以及他的兒子和朱夫人,最後一對窯主夫婦。千年窯火與南宋一起熄滅,與岳飛、文天祥、辛棄疾一起熄滅,為的是留取半山的乾爽,來侍奉那一批古書,文化的遺脈。但遺脈至今沒有找到,這裡邊埋藏著太多的未知,爸爸細緻,會有耐心去一一探詢。
無論如何,那個初春的夜晚,上林湖邊隨著一對年輕夫婦的喊聲,窯火一一熄滅時的景象非常壯觀。我想,從今以後,爸爸只要看到夕陽沉入上林湖時的淒美圖景,都會產生聯想。
隔著一條山路,對面的山坡上有一長溜平展的墓台,那裡留下了我家的另一段歷史。四年前我與妻子來拜掃時長草沒身、路徑難尋,便修築了這個水泥墓台,以及通向墓台的一條水泥小路。
東首第一個,是文革期間屈死在安徽的叔叔余志士先生的墓。我說過,叔叔出生在上海而不喜歡上海,工作在安徽而不喜歡安徽,獨身一人,尋找潔淨處所。這兒,就是這美男子的人生終點;
第二個,是伯伯余志雲先生的墓。他去世太早,我沒有見過,但他留下的一箱子書為我的草昧童年打開了一個大門;
第三個墓最大,是祖父、祖母的了。祖父早逝後,由祖母挑起全家重擔又走了整整半個世紀,但讓我們不安的是,墓碑正文上沒有這位偉大女性的痕跡,只有在旁側石刻碑記上提及「毛氏」二字。這是此間祖輩的風尚,到了父輩,墓碑上就會並列夫妻的姓名了。我想過很多補救辦法,都不行,何況我們確實也不知道祖母的真名。這個墓的碑文和碑記,都是外公寫的,書法很好,得意於柳公權和歐陽詢之間;第四個墓是外公自己的了,碑文是他自己寫的,筆觸已很衰疲。外公落魄一生又詩酒一生,與我們這些晚輩都嘻嘻哈哈,因此我們從東到西一個個拜掃過來,到他這裡就悲氛大減,都微笑著給他老人家上香。
墓台就這麼長,兩端都很難延伸,因此爸爸的墓只能安在對山。當然也有另一個理由,對山上面還有曾祖父余鶴鳴先生和曾祖叔父余鶴生先生的墓。祖母曾囑咐爸爸要年年祭掃,又特別關照,曾祖叔父終身未娶,祭掃時不可怠慢。爸爸聽話,把自己的墓安排在祖輩腳下。
聽長標舅舅說,我的表哥王益勝先生的墓,也在祖父、外公的同一個山坡上。但今天上山的人很多,有好幾位已經勞累不堪,也就不去尋找那個太悲慘的戀情故事了。
當年,當我們還都是小孩的時候,是我第一次帶著益勝哥進山的,把他嚇得不輕,慌張逃出。現在,他早已成為這座山的一部分。
造成這個悲慘故事的另一個主角,表哥的母親,我的姨媽,其實更加悲慘。她也安葬在此山,卻沒有葬在她兒子的邊上,這曾經使我很難理解。現在我理解了,她晚年一次次在這裡飲泣,似乎覺得兒子不會原諒她。但她永遠不會離開這個山坡,最後把無窮無盡的後悔,埋藏在別人很難尋找的荒草間。
長標舅舅說:「她自己選定的墓地,柴草都高過了頭頂,腳下蟲禽太多,誰也進不去。」
姨媽的自我懲罰,非常殘酷。
︱我站在山口,看著、想著這一宗宗前輩的墳墓,突然如獲神諭。山道兩邊,是兩頁斜斜的山坡,這便是一本碩大無比的古書,每個墳墓都是一段祕語,寫在草樹茂密的書頁上。這本書有舊章又有新篇,但整個說來,仍是一本古書。
這便是「吳石嶺裡藏古書」。
六、
辦完事下山,大家去了朱家村。
我們扶著媽媽,很快找到了那個直到今天看來還有點氣派的宅第。宅第早已換了主人,門窗都關著,敲門無人。但四周的鄰居聽說我媽媽回來了,全都趕了過來,一片歡聲笑語。
記得小時候每次跟著媽媽來外婆家,總讓瘦小的外婆忙壞了,不知找什麼招待我們。當時這一帶有一個糖挑子,賣一種盤在木板上,灑著白粉的麥芽糖。賣糖人一路敲著鐵鑿子,聽起來非常清脆。那時鄉間很少有貨幣,只用家裡的舊衣、舊布換糖。外婆家畢竟是從上海來的破落財主,舊東西多,一旦來客,糖挑子聞訊就過來了。外婆一聽到鐵鑿子的聲音,便翻箱倒櫃地找,然後樂呵呵地拐著小腳向糖挑子走去。
買糖人從外婆手裡接過舊衣、舊布,抖開來,在陽光下細細看一遍,塞進挑子下邊的竹簍裡,然後揭開遮在竹簍頂面上的一塊灰布,露出一大盤麥芽糖,把剛才沿路敲打的鐵鑿子按下去,用小榔頭一敲,叮、叮幾聲,削下一小片,又一小片。外婆伸手拿起,分給我們。
我後來一直覺得,帶走這個宅第最後一絲豪華遺跡的,就是那個糖挑子。正是在這裡,我們把大牆內僅留的一點往日驕傲,含在嘴裡吃掉了。
腦海裡正迴響著叮、叮的鐵鑿聲,卻聽到我妻子馬蘭和弟媳吳敏在邊上議論:「這位老太太真漂亮!」
我順著她們的目光看去,只見一位身材瘦削的老太太與媽媽摟到了一起。這位老太太與媽媽年齡相仿,也該八十歲了吧,但臉面清秀而乾淨,笑容激動而不失典雅,這是鄉間老太太中很少見的。而且,我覺得依稀面善,卻想不起是誰了。
我走了過去,問:「媽,這位是誰啊?」
媽媽連忙把我拉到老太太眼前,說:「逸琴,這就是我的大兒子秋雨。」然後轉頭對我說:「王逸琴,你記得嗎,和我一起去教書的王逸琴!」
啊,原來是她。
媽媽當年抱著我敲開她的家門,說自己嫁過去的余家高地地全是文盲,要她一起去義務辦班教書。
不久,我家堂前,余家祠堂,就有了兩個夾著書本、穿著旗袍的美麗身影。
她們當時那麼年輕,卻試圖讓王陽明、黃宗羲留下過腳印的原野上,重新響起書聲。她們成功了嗎?好像沒有,又好像有。
這是土地的童話。今天,童話的兩個主角重逢,卻都已八十高齡。
我,就從這個童話中走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