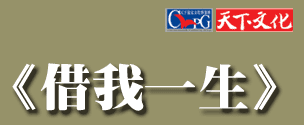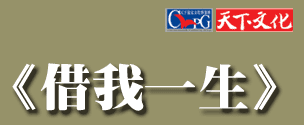三、
有一天吃完飯,我和妻子與兩位老人閒聊。我把氣氛調理得很輕鬆,然後請岳父談談回憶錄的寫作,尤其想聽聽與妻子有關的內容。
以前,我只知道他們在縣城挨批鬥時把五歲的馬蘭和兩個哥哥送到舉目無親的葉家灣躲藏的事。
岳父說:「她出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來還非常感動。」
馬蘭出生前,兩個哥哥已經餓得皮包骨頭,特別是小哥哥,幾乎快不行了。做父親的和其他很多右派份子一起在水庫工地上服苦役,毫無辦法。一個幹部走過來,要岳父把這個孩子送給他。岳父搖頭,幹部說:「你這麼個右派份子,怎麼養得活兩個孩子呢?」這話刺激了周圍的右派份子,等幹部走後,一人湊一斤糧票,這在當時等於是割膚捐血。岳父接著再湊錢去買粗糧,全家活下來了,這才有後來的馬蘭。
說到馬蘭,岳父高興了。他說:「受罪的人也會有很好的後代。老伴懷馬蘭時,我就天天到河裡摸魚,保證營養。所以我在回憶錄裡向天下夫妻傳授經驗:要生一個漂亮一點、聰明一點的孩子嗎?妻子要多吃魚,而且要丈夫下水親自摸!」
我們一聽都笑了。岳父還在說:「但是要培養成為人才,還有很多門檻。有一條最關鍵的門檻,是她跨的。」他指了指岳母。
岳母知道他在說什麼,便接著回憶下去。
說的是,馬蘭十二歲時初中畢業,考上了省藝術學校。全部複雜的手續都由她這個小女孩自己辦完,但遇到了最後一條門檻跨不過去了:她是右派份子的女兒,政治審查通不過。
對此,岳父本人沒有發言權,因為事情的起因就是他。但他還是連夜寫了一封封的申訴信。學校從錄取到報到的時間很短,這些申訴信往哪兒寄,寄了有沒有效果?
岳母也是一個演員,平日不會對任何人說半句重話,這天她跟著劇團在一個山區演出,聽到這個消息後悲憤交加,決定破罐子破摔,不幹了。劇團領導勸不住她,只好請來在當地下放蹲點的一個革委會祕書。
革委會祕書指了指山坡上連綿的火把,說:「你看,遠近幾十里的鄉親們都舉著火把來看戲了,主角演員罷演,這可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說:「那你們就把我打成反革命份子好了!我女兒考上了學校卻不准上學,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革委會祕書又抬頭看了看暮色中的群山,火把越來越多,遠遠看去望不到頭,像一條神祕而光亮的長龍。他覺得今夜如果不開演,真有可能釀成重大事端,態度就軟了下來:「這樣吧,你女兒上學的事,不難辦,我明天一定給革委會主任說。」
「我很難相信你們。」岳母說。
「那我現在就向你保證,一定讓你女兒上學!」一個祕書就這麼作了決定,這就是文革。
「你說了不算數。」岳母還是很硬。
「那我現在就出發去找革委會主任,你上台!」祕書急了。
「那好,你出發,我上台!」岳母說著也看了看山路。祕書逆著火把的隊伍出發了,她也開始化妝。
幾天後,十二歲的小馬蘭拖著一個大木箱,裡邊塞著棉被和棉襖,擠上長途汽車向省城出發。岳父、岳母都分別向自己所在單位請假,說女兒實在太小,省城實在太遠,希望能送一送。兩個單位都不批准。
這次長途汽車,坐了整整八個小時。
四、
聽兩位老人說完,我對那曾經延綿過火把長龍的青山,產生了渴念。
青山下,還會有湊糧票的右派份子們挖的水庫,還有庇護過五歲馬蘭的葉家灣…… 妻子對我的這種渴念很感動,說:「那就去一次吧,順便掃一掃長輩們的墓,好在都不在省城。」
於是,我們一頭撲回到了青山大湖之間,撲回到了妻子十二歲之前留下過腳印的全部地方。
妻子踏入葉家灣時腳步非常小心。這是她五歲離開之後第一次回來,當年接收她的葉小文大爺還身體健朗。她還能記得幾乎沒有什麼變化的池塘、土坡和泥牆。見到圍過來的鄉親她不斷致謝,感謝這個小村莊讓她在大難中借住了一段永生難忘的時光。
和我一樣,她後來以最長的時間借住在一座城市,而且很對得起那座城市,但那座城市在情義上,遠不及這個小村莊。
「大爺,從縣城過來那麼遠的路,當年你是怎麼把我馱過來的?騎在你肩上嗎?」妻子問葉大爺。
「不,是坐在拖蔬菜的板車上,也有一半路是你自己走的。」大爺記得很清楚。
「我記得滿路都是野花。」妻子說。
縣城叫太湖,我們仔仔細細地看了那些街道。今天,這些街道以巨大的熱忱歡迎我妻子的回來,古樸的石巷旁擁擠著最醇厚的呼叫和微笑。
妻子說:「其實爸爸、媽媽到這裡,也是借住。太湖已經靠近湖北,對省城來說實在太遠,爸爸大學畢業時分配工作,被一個有背景的人『調包』,糊里糊塗到了這裡,以前連這地名也沒有聽說過。媽媽更有趣,在安慶的一所女子中學畢業時聽說太湖招募演員,以為是江蘇的名勝太湖,興高采烈地來了,那天在這個小縣城住下後還問,明天到太湖還要趕多少路?」
「於是,小縣城裡文化最高的小伙子,遇到了小縣城裡最漂亮的女孩子……」我開起了玩笑。但這兩個「最」,倒是來到這裡後一再聽當地老人們說的,不是我的誇張。
「問題就出在這裡。」妻子說:「我後來一直聽很多大叔、大媽感嘆,爸爸被打成右派份子受難半輩子,什麼罪名也沒有,只因為他大學畢業,而媽媽又漂亮了一點。人們見不得美好,更加見不得兩種美好的結合,覺得太刺眼了,就要想著法子來暗掉。」
「你好不容易到省城讀藝術學校,頭上一直頂著『右派子女』的帽子吧?」我問。 「處處矮人一截,只能低頭用功。」她說,「在集體宿舍,一位女同學說,她的床飄得到雨,要與我換,我也覺得理所當然,立即換。」
我一算,那時間,正好是我爸爸病危,醫院和單位因他是「打倒對象」而不給會診,我瘋瘋癲癲地到處奔波而求告無門的日子。而且,也是這些年那幾個酒足飯飽的大批判幹將們憑空誣陷我有「歷史問題」的日子。
這時我們已站在縣城到省城去的路口。妻子說:「那夜大青山上鄉親們的火把長龍救了我,讓我走通了這條路。現在才知道,並沒有走通。」
「我也沒有走通。」我說。
天已薄暮。我們抬頭,青山依舊,卻不知今夜,還有沒有一、二個火把閃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