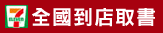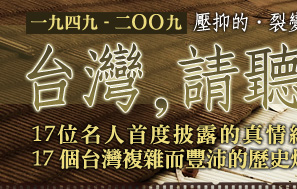我的母親是陝西古老滿清的正白旗貴族,曾祖父是西安知府,她生在一個好家庭,從小看戲班唱戲、讀演義小說,很有文化教養。而我父親是福建農民家庭出身,他們的結合很特別,一個天南、一個地北,又各自屬於不同階級。我媽媽家是老貴族,有很多房子租給人,我父親去做我母親家族的房客,兩人後來就相識結婚了。
我出生在西安,一九四九年,也就是我三歲時,和父母兄姊輾轉經由馬祖白犬島來台。我的父親是糧食局的公務員。我們家有六個兄弟姐妹,我排第四,但我們共同的記憶是,我們很少得到爸爸的鼓勵,他永遠跟我講做人處世的道理,永遠問我功課做完沒?他總是要求孩子要做得更好。
嚴父慈母是有趣的,在我父親面前,我會像賈寶玉看到賈父會發抖。我母親比較柔軟,我一直到了五十幾歲還躺在母親懷裡,讓她幫我掏耳朵,在她面前我完全可以撒嬌自在,好像賈寶玉在賈母面前,極其驕縱,賈母可以用手從頭摸到背的那般溺寵他。
我小時候跟母親一起去市場買魚、買蔥、買薑啊,回來剁豬肉、糅麵糰、桿麵皮、包餃子,然後一起吃。食物原本是一種滋養分享,我和媽媽所有的味覺、嗅覺、觸覺都在一起分享。
但這些美好時刻,感覺我父親常常是缺席的。他常晚歸回來,然後吃我們吃剩的菜,只是盡責任在餵飽自己。他是農民家庭出身,從來不懂享樂,連電影都不太看。我國小時他帶我去吃麵,為了省錢,他自己叫一碗陽春麵,卻叫豬肝麵給我吃,我當時覺得好羞恥。
我始終搞不懂,父親為什麼要扮演那種刻苦勤勞的角色?他晚上睡在 三十公分 寬的條凳上,一夜姿勢不變,絕不會掉下來。我早上起床後,他已經在掃地,不管什麼時候,寫的字永遠一絲不苟。
可是我母親不會這樣,她會去偷偷看電影、買化妝品,有一種做為女人的、小小的快樂,我也分享了她那個部分。而我父親永遠不懂我母親為什麼要去聽戲、看電影。
我對父親一直只有尊敬,甚至敬畏。一個人如果你看不到他犯錯或脆弱的時候,那是永遠不容易親近的。所以當八十七歲去世時,我有一種好複雜、好難講的心情,有儒家式遺憾的彌補,也有西方父子衝突的復仇,既愛戀又憎恨,既依戀又報復。
清洗父親的遺體,其實也等於我清洗了我自己。這其實是一種儀式,他走之後,我畫了一系列男體油畫,探索肉身,探索自己,也探索父親,慢慢跟他有種精神上的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