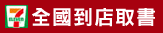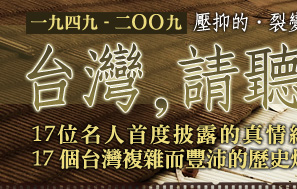一九八七年,台灣終於解嚴,但威權仍在,我申請回台,但國民黨政府要我寫「回台後保證不參加政治運動」切結書,我只好拒絕。拖了二年,到了八九年六月,他們終於給了我「中華民國護照」,可以用「思想犯」身分回台。
這本「中華民國護照」很特別,好像專為「思想犯」準備的,一般人都是M開頭的,它是X字母開頭的,他們說:「如果你不寫切結不參與政治活動,那就用口頭講!」原來他們準備好攝影機,想用攝影存證。我不要,這樣太羞辱我了。僵持到最後,我只好用美國護照入境,他們特別用「中文」(不敢用英文)在我的美國護照上加注:「限五月三十日入境,六月三十一號出境。」
當飛機要降落時,即將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台灣,我第一次感到什麼叫做「近鄉情怯」,要回到十五年未見的台灣,心情好激動,我出國時,還在台北「松山」機場,再回來,飛機卻要降落桃園。我們常講「近鄉情怯」,但只有到那時我才體會到……。那個感情,不知怎麼定義,很複雜,非常複雜。
當飛機慢慢下降,降到一個高度,在空中繞著大彎時,我終於看到機場附近的青色山脈,啊,……我眼淚就掉下來,我孩子坐我右手邊,我趕快把頭別過去,不敢讓他們看到我的臉。
我一直看著窗口,看飛機一路下降,心裡好激動。我下飛機出關時,看到那麼多人,我…我面對他們,一句話都講不出來。很多朋友來歡迎我,記者也都在等我發表感想,原本我想要講的:「我很高興回來…」。但事到臨頭,我卻什麼都講不出來,完全不知要講什麼。
那個時候,大哥大還是黑金鋼這麼一大隻,我看到特務戴著草帽,拿著黑金鋼跟著我。我有點生氣,朋友說「不要理他」,敢快把我拉走。
我回到故鄉左營,我父母說,原本他們還擔心我會被捉去,看我踏進門,他們才放心。我回到故鄉後才知道,原來調查局每個禮拜都到我家。回家第三、四天,我要出去剪頭髮。我父親說:「你等一下,待會兒李先生要來嘿!」我很疑惑地問:「哪一個李先生?」聽他的語氣,好像這個人跟我父母很熟。原來他是調查局的李某,常來我家跟我爸媽說:「你兒子在美國又寫些什麼文章,我都知道。」
我聽了之後很生氣,幾乎是暴怒地責備父母:「你為什麼讓這個人坐在我們家的客廳?」我很氣,並堅持要去剪髮。
後來李某來了,我問他:「幹嘛做這種事?」他說:「只想知道你對政府的態度?」我回說:「你調查局的,不知我對政府的態度?以後有事找我,不要找我父母。」我去剪頭髮,把姓李的撂在那裡。
剪完髮回家,父母親低聲下氣對我說:「欸,你不要這樣啦,我們還要在台灣生活下去嘿?」語氣近乎求情,那時候我才知道我對家裡的傷害,原來他們過著這樣生活。那一刻,我感到非常、非常挫折,你想要改造台灣的命運,但台灣還沒有改變,就已經先改變了你家族的命運了。
回台後,我每一場演講都被特務緊跟,一月個後,我被迫離開台灣,有一種被驅逐出境的羞辱感,但我知道,有一天我終將回來。
(摘自陳芳明:該是島內和解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