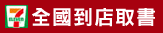|
「我的幼年是無文的世界。」齊先生以如此驚人之句起筆,寫自己的成長遇難。誕生於當時多難的東北,她的父親一生懷抱愛國愛鄉的理想,公而忘私,與家人離多聚少,多賴母親辛勞持家。對於母親,她有很深的同情,對父親則始終敬佩崇拜著。這個印象,從訪韓旅邸寒夜的初識對談時,我就感受到。在我們交往的三十年裡,斷續或重覆的話題中,關於齊世英先生從事東北的地下抗日工作、創辦主張民主自由的雜誌「時與潮」,以及政治生涯種種,每一次的談話裡,我都聽出她由衷的崇仰之情。而這一份崇仰之情落實為文學記述,遂由敘載之詳實呈現出來。於成長、逃難、求學的青春歲月,父親的影像無時不在,籠罩著整個前半段;甚至更及括後段渡海來台以後。父親的公正無私、堅毅勇敢,及明理智慧的人格特質,對她影響至深,是作者一生追隨的典範。
在大陸的年輕歲月裡,另一位對作者影響深刻的人是武漢大學外文系的朱光潛教授。朱先生當時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平時表情嚴肅,講雪萊的「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用手大力地揮拂、橫掃……口中念著詩句,教我們用“THE MIND’S EYE”想像西風怒吼的意象(IMAGERY)。」這種對於文學的熱情和專注,啟發了青春學子的心靈。「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詩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盡。」作者這樣寫著。從離亂戰爭的學生時代,直到戰後來台教書,甚至退休後的今日,對於文學的靈敏度和熱情始終燃燒未熄止。一位良師對於學生的啟迪是多麼深遠可貴啊。只是,又有幾個學生會這樣細膩精緻地拈出良師的特質呢?前此,我也曾經聽她幾度談及衷心敬佩的「朱老師」,然而這短短幾行字卻重新帶給我生動感人的印象,則文字的力量又是多麼深刻巨大啊。
如果以炮火下輾轉逃難,個人家族和整個國家都與多事多難的時局攪拌不可分割,而概括二十三歲以前為大陸經驗的話;由於偶然機緣漂泊來台的「外省人」,在此成家立業,踏踏實實生活了六十年,見證台灣的發展,並且從文學的角度參考、推動文化發展,渡海後的作者已然成為不可自外於「本省人」的外省人了。
和羅裕昌先生相識於台北,徵得雙親同意,回上海結婚。新婚十天離開「人心惶惶」的上海,兩人再來到「海外」的台北,組成了小家庭。成為羅太太的作者,從此住在羅先生任職的鐵路局宿舍,隨夫婿調任,由台北而台中而再回台北,二十年間,南北遷移。
羅先生是體格高大的四川人,話不多而聲音洪亮沉穩。大學時主修電氣的他,予人誠懇明智的印象。五十年代的台灣,局勢斷趨穩定,政府開始改善人民生活,各種大型建設在那個時代施行。日治時期的鐵路運輸系統已不敷現代需求,羅先生率先想到把美國中央控制車制系統的新觀念介紹來台灣。他們夫婦兩人於下班忙完家事,哄睡孩子後,燈下將美國鐵路協會出版的「美國鐵路號誌之理論與應用」譯成中文,成為工程人員必讀之書。調職任鐵路局台中段長的羅裕昌先生,是策畫者,也是施工主持者。
「灑在臺灣土地上的汗與淚」記述了有關此重要工程進行前前後後的事情,在書中佔著相當大的比重。今日台灣的居民理所當然的享受著鐵路全自動控制的便捷與安全,多數人不知在建設時經歷幾許辛勤緊張的代價。放假日不分晝夜的工程,在戶外施工無法抵擋風雨,遭遇八七大水災,更造成未完工先摧毀的嚴重打擊。工作人員邊建設邊搶修,日夜不休,吹風泡水。身為主其事的羅先生率先眾工人「打拼」,為時長達數年。整個始末過程,書中沒有誇張形容,羅列一件件可驗證的事實,可謂台鐵全自動控制化的歷史﹔然而作者身處期間,於事實的冰冷陳述之外,更多了一份側寫台鐵員工上下人員,及其家屬的身心感受,則又豈是台鐵官方歷史所能盡書的?其後,鐵路局調羅先生北上,參加國家十大建設鐵路電氣化計畫工作。一九七五年電氣化現代工程輝煌完成,他獲領五等景星勳章,聘為國家建設研究會研究員,但他的耳朵卻因長期過勞睡眠不足而嚴重受傷害,退休時聽力只剩十分之一、二。
隨著夫婿南遷復北上的作者,始終從事她熱愛的文學教育與推展工作。我和她得以相識乃至深交,也是因對文學的共同喜愛與關心的緣故。我在台大中文研究所開「六朝文學專題研究」課;而她的「高級英文」是中文研究所和歷史研究所的共同必修課,所以選修我課程的學生,當然也是她的學生。我常常從學生口中聽到齊老師嚴格而熱心的教學風格。一九八五年,她從麗水街的家出門,在師大人行道等計程車,突然被橫衝來的摩托車撞倒受重傷,左腿骨折,住進三軍總醫院手術治療。學生們去探病,事後她告訴我:「那些學生們是參加喜宴後來看我的,個個衣履整齊漂亮,讓我覺得很光彩!」而出院後我去麗水街,竟看到她坐輪椅中,把膝蓋下植入鋼釘、上了石膏的腿平舉,手邊猶校改著筆會季刊的文稿。「現在你是『鐵娘子』了啊。」一時心疼且感動,不知說什麼好,我只得說笑。「『鐵娘子』還背英詩療傷哩。」她也回以說笑。我想,文學已經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了,而是血是肉了。
是血是肉,與身心不可分隔的文學。就是這樣的狀況促使她背詩、教英詩,關懷台灣的文學。多少年來齊先生所寫的評論,從個別的作家,到整個的文壇,總是受重視。她的文章是品評,也是指引。獨創的「眷村文學」、「老兵文學」、「二度漂泊的文學」等詞彙,已成為台灣現代文學史上的特定指稱,被普遍引用著。
對於台灣文學,她不僅止於賞析評論,經由筆會季刊、蔣經國基金會的台灣文學英譯計畫、稍早與張蘭熙女士合作、目前和王德威共同策劃,持續有方向地譯出許多當代具有特色的文學作品。二○○三年,「國家台灣文學館」在台南的馬兵營故址開幕,是她提議、鼓吹多年的成果。館長與副館長都是台大出身,眼看著「我們台灣的文學」教育與保存發展都有了晚輩穩健接續,齊先生很高興地笑了。「很快樂。」這是她滿意的時候慣說的口頭禪。曾任副館長的陳昌明是我們兩個人的學生,他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過:「放眼台灣現代文學的研究,處處都有她不可抹滅的影響。」
「我的快樂是自備的。」這也是她常說的一句話。齊先生的快樂是自備的,因為許多年來她熱情而堅毅地耕耘著文學的土地,遂有了豐滿的開花與結果。如此,那源自巨流河的水勢,到啞口海沒有音滅聲消,看似平靜、實則洶湧未已。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