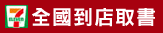|
經常以「咱們台灣人」作為口頭禪的台灣文學界恩師齊邦媛女士,費時四年完成的大著《巨流河》(天下文化發行),是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也是一部過渡新舊時代衝突的女性奮鬥史,同時是一部台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紀,更是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該書的發表茶會,訂於明天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三時三十分,在台北市松江路93巷2號「人文空間」舉行。本刊特於今明兩天,精摘《巨流河》中有關教學與譯述的部份,讓讀者先行領略齊老師的春風時雨。──編者
接任筆會主編
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的一天早晨,蘭熙家人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立刻去她家一趟?我到她家書房,看到她雙手環抱打字機,頭俯在打字機上哭泣。她抬頭對我說:「邦媛!我翻不出這首詩,季刊下一期要用,我怎麼辦?」那是白靈的短詩〈風箏〉。過去整整二十年間,季刊大約英譯二百多首台灣新詩,幾乎一半是她快快樂樂地譯作,如今蘭熙出現失憶現象。當時無可奈何,以承受好友陣前託孤的心情,我接下筆會英文季刊的編務。
以前只知道蘭熙經常用殷之浩先生支票付款,我接編後,殷先生病中,尚主動送五十萬元至季刊,宣揚文學成就。政治和文化政治刊物,有新聞局、外交部每期買數百本贈送友邦,箋箋書款便是我們全部的收入。文建會有一位頗為「同情」的專員私下指點我們,可以「文化遺產專欄」計畫前往申請補助,所以我請曾上過我台大「高級英文」班的藝術史組的學生顏娟英和陳芳妹,輪流為季刊每期寫一篇英文論文。顏娟英在哈佛得學位,回國任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由「唐代佛教之美」寫起;陳芳妹在倫敦大學得學位,回國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由「家國垂器──商周貴族的青銅藝術」開端,一直寫了十年,助季刊得到文建會補助印刷費。
最艱困時,好友文月代為申請得到她的父親「林伯奏先生基金會」補助部分稿費等。有兩次助理月薪發不出來,隱地私人捐助渡過難關,筆會有一個堂皇的理事會,定期開會而已,對於我實際的困境,只說「能者多勞吧!」聚餐結束各自回到舒適的本職。我滿七十歲的時候,實在身心俱疲,請理事會務必找人接替,他們嘻嘻哈哈地說:「你做得很好呀,人生七十才開始啊。」說完了又散會了。
我在筆會季刊快樂地建立了一支穩健的英譯者團隊,我們稱為「the team」。最早的一位是康士林(Nicholas Koss),他在一九八一年初到輔仁大學英文任教時,由在台大兼課的談德義(P. Demers)介紹給蘭熙和我。康教授是天主教聖本(St. Benedict)篤會的修士,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專修比較小說、西方文學中的中國、宗教與文學、華裔美籍作家作品研究、中英翻譯小說。我接任主編後,他是我最可靠的譯者與定稿潤飾者,我所寫的每期編者的話 (Editor’s Note)都請他過目。日後我經手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編譯的書裡書外,他也都是我第一位讀者(英文「reader」,亦有校閱之意)。近二十多年間,我們小至字斟句酌談譯文,大至讀書、生活,一見面就談不完。他知道我多年來以珍.奧斯丁《傲慢與偏見》(Jane Austin,Pride and Prejudice)作床頭書,身心得以舒適,每到英美旅行、開會,常給我帶回各種版本、錄音、錄影帶。二○○○年我讀到柯慈(J. M. Coetzee)的新作 《屈辱》(Disgrace),大為此書創意所吸引,堅持他抽空讀一遍,我們可以好好討論一番。擁有真正是比較文學的文友,實在難得!
輔仁大學另一位加入我英譯團隊的是歐陽瑋(Edward Vargo)。他擔任輔仁外語學院院長時,與康教授熱忱推動的翻譯研究所,一度遭教育部擱置,蘭熙與我曾到高等教育司陳情,力言翻譯人才學術培育之重要,終得通過。該所第一、二兩屆的畢業生皆極優秀,如吳敏嘉、湯麗明、鄭永康、杜南馨皆為筆會季刊英譯散文,小說與藝術家評介逾十餘年,我們看到了培育的花果,滿是欣慰。
在那許多年中,我當然知道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長篇小說的英譯,就缺少了厚重的說服力。所以一九九○年,文建會主任委員郭為藩先生邀集「中書外譯計畫」諮詢委員會時,我欣然赴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提出建議,大家開出待譯的書單、可聘的譯者和審查者。開會十多次,每次郭主委都親自主持,認真傾聽,討論進行的方式。文建會也確實編列預算,突然郭先生調任教育部長,接下去五年內換了三位主任委員,每一位新任者都邀開同樣的諮詢會,但都由一個副主委主持,先把前任的會議紀錄研究一番,批評兩句,修改一番,敷衍些「謝謝諸位寶貴的高見」的小官僚話,然後散會。這樣的會開到第三次,我問那位主持社區文化專家的副主委:「為什麼要重複討論已經議定的事項?」他說:「換了主委,遊戲規則也得變。」我說:「我很忙,不與人玩什麼遊戲。」站起來先走了。從此不再「撥冗」去開那種會,對台灣的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
從筆會季刊創刊起,我便是長年效力的顧問,但是自己太忙,從未過問它的實際業務。一擔挑了近十年!那十年的得失怎麼說呢?我一直在等待,觀察懇求可能解救我的接班人,但是那是一個沒有經費、沒有編制、沒有薪水、沒有宣傳,也沒有掌聲的奇怪工作。比我晚一代的好手,稍作考慮即感到這樣的獻身,甚至不知為誰而戰,都說太忙而拒絕接手。事實上,我早該明白,我一個撐著這本刊物是件超級寂寞的工,真正的作家都是「單槍獨行俠」。筆會原是以文會友的組織,但是蘭熙退休後,她所建立的國際友情,如英、法等筆會原創人已漸漸凋零。
一年復一年,我對筆會季刊的感情好似由淺水一步步涉入深水,直至千禧年前才得以解脫。不捨之心是有的,但是歲月不饒人,解脫就是解脫。我曾經揹著軛頭往前走,所完成的當然是一種唐吉訶德的角色。
鼓吹設立國家文學館
國家文學館之設立,是我以個人微羽的力量,向政府文化政策所作的最後一個挑戰。一九九八年三月底,報紙有一篇報導立法院審查會擬將多年的國家文學館附設於文建會「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不能獨自設館,或亦可將它附設於大學院校一事,令我感到學術界又受一次政治愚弄。因遠在七年之前,文建會由黃武忠先生等人策畫,請我與四、五位專家學者,多次頂著大太陽前往台中、台南、高雄等地探勘館址,同行者有羅宗濤、陳萬益等中文系教授。經過半年的討論,決定在台南設館,然後就被他們延擱多年,如今竟是這樣!
第二天上午是九歌出版社二十周年慶祝會,原已邀我作「貴賓致詞」,當晚我思索許久,決定在賀詞之外,為這件事說一些話,這不該是我一個人的憤怒。這樣的聚會就是真正的文壇之會,許多人已知我多年。我在會場詳細說明自己與這件事的因緣和所耗時間和心血,唯一的期望是給我們的文學一個「家」,絕不能與古蹟、文物、保存技術等混在一起,在衙門的屋簷下掛一個孤伶伶的牌子,收藏一些發黃的手稿。因為在台灣這樣的政治環境,只有文學是超然的,或能不受政黨、經濟的影響。如果定名為國家文學館,台灣未來是統是獨,它有文學的尊嚴,任何搞政治的,也沒有膽量推翻一個「國家」。我一場慷慨陳詞不但引起與會文友的熱烈反應,第二天四月一日,各報都有相當顯著的報導。《聯合報》文化版以很醒目的標題:「不設國家文學館──文學之恥」強調此館之重要,並且附了一張我在麥克風前握拳大聲疾呼的照片,以半版的篇幅寫作家的發言,和設館乖舛的籌備過程,反映了政治現實妥協下的荒謬……。
這些聲音確實產生效果,不久我們即收到立法院幾位文化立委和教育立委召開聽證會的邀請函,我認為自己公開呼籲已說明了中心盼望應該有更多的聲音和力量,在會前我寫了一封信給向陽(林淇瀁先生),希望他們以詩人的洞見(vision)加強我提出的中心意象,我這樣寫:
當人們說到「文學殿堂」時,有時會有嘲諷之意;但想到文學館,我認為它在教化的功能上應有殿堂的莊嚴涵義,所以不宜與別的實用工作組織擠掛一張牌子而已。
這個館應該有一個進去就吸引人的明亮的中心,如大教堂的正廳穹蒼圓頂,或現代的展示核心,用種種聲光色電的技術,日新月異地說明文學是什麼?圍繞著它的是台灣文學的成績與現況,世界文學的成績與現況,在後面是收藏、展示。它不是一個死的收藏所,而是一個活的對話!進此門來能有一些啟發,激盪或更多的思索,至少不空心出去。
這樣具有象徵意象的館,也許不是目前所能建立的,但是往長遠想,我們應該先說明或描繪一個真正的理想,也許政府,乃至私人捐募,可以有日建出一個有尊嚴獨立的國家文學館,遠超政治之上。
我知道現在的文建會林澄枝主委已盡心盡力在獨立設館的爭取,盼大家共築遠景!
向陽是文字靈活,意境卻沉穩的年輕詩人,筆會季刊譯者陶忘機英譯他的「春、夏、秋、冬」四個系刊的長詩,所以是可以談話的朋友,也了解蘭熙和我對「我們台灣」愚忠心情的年輕文友。他曾主編自立晚報的〈自立副刊〉,更重視台灣文學的處境。同年他也寫了一篇火力全開的〈打造台灣文學新故鄉〉,為文學館催生,我們大家最怕它在所謂「文化政策」下只是一個角落裡掛著的一個牌子,喪失了文學應有的尊嚴。也許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二○○三年十月,由台南兵馬營舊址整修而成的,新名為「國家台灣文學館」燈火輝煌地開幕了。我在新聞報導中看到,首任館長成功大學教授林瑞明(詩人林梵)和副館長陳昌明(成大文學院院長)竟都是我台大高級英文班上的學生!這一座曾經歷史滄桑的建築,如今堂皇地以文學館為名,站立在遺忘與記憶之間,總比個人的生命會多些歲月,具體地見證我們的奮鬥與心跡。
近年來台灣已有十多所大學成立了台灣文學研究所,自清華大學的陳萬益教授,成大的呂興昌教授等創系人,到較新成立的政治大學陳芳明教授、中興大學邱貴芬、台大何寄澎、柯慶明、梅家玲教授,都是我的學生。有時看著各種會議的議程以及論文主題,真覺得那些年我在教室的心血,算是播下了種子吧!那一刻,我想高唱聖歌《普天頌讚》三六五首:「埋葬了讓紅花開遍,生命永無止息吧」。
而我多年來,當然也曾停下來自問:教學、評論、翻譯、作交流工作,如此為人作嫁,忙碌半生,所為何來?但是每停下來,總是聽到一些鼓聲,遠遠近近的鼓聲似在召我前去,或者那仍是我童年的願望?在長沙抗日遊行中,即使那巨大的鼓是由友伴揹著的,但我仍以細瘦的右臂,敲擊遊行的大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