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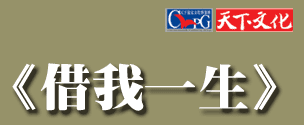
余秋雨 叩問傳媒 最起碼的職責︰真實 Q:你在《借我一生》書中有一段話,談到你在父親生前一直把真實處境瞞著他,瞞得他放心。現在他一走,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回頭一看,終於知道你這些年是在罵聲中度過每一天的,年年都成為中國文化界被罵得最多的人。你說父親一定會在冥冥中焦急地問,「他們究竟是誰?」其實關心你的讀者也有這樣的疑問,「他們究竟是誰?」
第二個是湖北的古某,「金牙齒」的密友。「金牙齒」得知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了毛澤東發動文革有嚴重錯誤,失去了「清查」我的理由,便急忙拼湊了一些我的其他「材料」,藏在家裡,隔了二十多年趁人們失記,叫古某逐一發表,釀成我的所謂「文革歷史問題」。我曾起訴古某,在法庭上完全搞清了他的所謂「材料」的來源。 第三個是上海的金某,在我的每本書上都「咬嚼」出了大量的所謂「文史差錯」。我寫書涉及範圍廣,差錯一定不少,任何人來指出都非常歡迎,但這個人卻一夜之間用爆炸式新聞的方式,把這件事情變成全國性的文化聲討,把廣大讀者無法判斷的文史細節推到大陸幾乎所有的傳媒上,而且公開表明這樣做是為了針對我的一篇反盜版宣言,他不僅要咬嚼我的文字,而且「還要咬嚼靈魂和骨髓」。 經不少讀者的提醒,我又瞭解了他在文革中的驚人歷史。我在路邊報攤上粗粗瞥過一眼他對我的「咬嚼」,除了一些排校差錯外,其他大多是他在張冠李戴、小題大做,或半懂不懂、似是而非。他的目的主要是賺錢。他知道我在台灣、香港有很大的讀者群,近來主打台、港媒體和出版社,收益頗豐。我規勸台、港的媒體和出版社發表他的文章和書籍前,派人查核一下字典,並查核一下我的原書。 跟著他們起哄的還有幾個,例如北京蕭某、湖南餘某和深圳朱某。只要我有一舉一動,他們就在媒體上大鬧一通,媒體也喜歡採訪他們。 Q:你也提出這些人的活躍,出自於「文化災難的復燃機制和蔓延機制」,請談談這些事件對你的影響。
於是六、七年下來,人人信以為真,我本人無從解釋,只能忍辱吞聲。甚至,我到吉隆坡、新加坡、巴黎、舊金山、布達佩斯、奧斯陸、赫爾辛基,只要有華人社區、華人讀者,都相信了他們的誹謗,只感到他們「態度不好」而已。 Q:在書中看到你跟古先生打官司的經過,但你的好意,似乎並未得到善意回應。如果再來一次,你會有不同的態度、做不同的決定嗎?
Q:這是過去,採低調處理;但是現在不少海外媒體透過網路消息做進一步報導,請問這些消息都確實嗎?你會回應嗎?
如果他們編造的這些材料確實,為什麼遲至三十多年之後才「揭發」出來?按照大陸的政治慣例,每次審查運動都大搞全民性的檢舉揭發,結果總是過嚴,只會嚴重擴大,而絕不會漏網。文革結束後追查文革中有問題的人,嚴到只要參加過造反隊,就不可能擔任最小的幹部,那麼,我怎麼擔任了高校校長呢?這是一個人人羡慕的職位,覬覦的人很多,他們如果要把我拉下,換上自己,只要向上級報告一點點「文革」中做的錯事,立即就會拉下來。我任職六年,上級從未收到過這種報告,當時災難剛過,一切記憶猶新,為什麼大家都放過了我? 現在,所有最過分的話都是我的被告湖北人古某說出來的,你看前兩天他突然說,張春橋接見過我。我說,如果在電視裡看到也算「接見」,那麼希特勒也接見過我。他又在香港的報刊上說,正在研究我「參與奪取最高權力」的問題,不知他所說的「最高權力」是指誰?毛澤東?鄧小平?還是現任的領導?他幾乎每個月都會「發現」我三十幾年前的大量「罪證」,而且據說都有「確鑿證據」,每次「發現」,傳媒都廣為刊登,「證據」也任憑他說。 我因為與他打過一個官司,知道他的精神狀態非同尋常,但今天在大陸卻成了「揭發英雄」。對這樣的指控我很難回應,因為我剛剛回應一句,他很可能就會宣布我「參與謀害了毛澤東」,或者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特務」,或者是「東條英機的高級參謀」。等看看吧,他的想像力比誰都豐富。正是這種想像力,使文革中全中國有幾十萬知識分子都成了「叛徒」「特務」「漢奸」,其中很多人沒有等到平反的一天。 Q:根據媒體報導你宣布「封筆」,退出文化圈活動、引起媒體與讀者關注。為什麼決定「封筆」;往後你的生涯有怎樣的計畫?
後來,還是台灣的朋友們勸阻了我,還送了我不少筆。我覺得確實還應通過考察歐洲文明來尋找中華文明的弱點,再寫一本生平記憶。 現在這兩件事都做完了,大陸文壇對我的糟踐和驅逐愈來愈厲害,往往隨手翻開一張報紙,總能找到惡言惡語誣陷我的文章,連「剝余秋雨的皮」這樣的文章也寫出來了,大家都知道這是那些想靠罵名人出名的人和嫉妒者們在胡鬧,但誰也幫不了我,誰也阻止不了這股塵囂甚上的狂潮,而我又不忍讓我的家人和學生一直處於這種侮辱之中,因此只能離開。 那個宣布從妓女提包中發現了《文化苦旅》的人,寫文章說我離開是「作秀」。其實真正理解我的讀者都知道,按照我的年齡和寫作狀態,現在離開實在是一個錐心泣血的無奈選擇。一對在非洲生活的華人夫妻從報紙上看到他們罵我的那麼多文章後,邀請我移居非洲,我想那就太寂寞了。但我實在不想再寫什麼,為此寧可讓朋友們責怪我退卻。今後做什麼,不知道。走著看吧。 Q:你在書中說:「要讓世界各華人社區的讀書人,特別是海峽兩邊的讀書人,都比較願意讀某個人的書,這種情形不多了。我既然碰巧成了這個人,那麼,也就承擔了一種話語使命。」這種「話語使命」與「封筆」代表著不同心境,你是否會對封筆之事再做考慮?
Q:你曾針對大陸媒體長期對你的不公報導,提出了七項質疑反擊。對於大陸媒體「向權威挑戰」的姿態,你頗有感觸,請你談談這個時代的「文化道義」。
那些媒體近十年來連續不斷地對我的誹謗,即便是從最低的道義關懷如同情、體諒,也絲毫無存。例如,我畢竟徹底的無權無勢,不是什麼「代表」和「委員」,連作家協會、文聯也沒有參加,沒有領取過「專業作家」的任何工資和津貼,一直辛勞不堪地在遙遠的危險地帶考察文化,年歲也已不小,每次考察都耗費很長時間,都要離別家人,我又從來沒有批評過別人,更不可能爭權奪利……這些基本情況,人人都知道,但他們發覺罵余秋雨最安全,就一年年、一月月、一天天地罵個不停。 我這次提出七項質疑,已經無關乎上述道義,只是最後一次來叩問作為傳媒的最起碼職能:真實。如果永遠地不講真實,我最後一次叩問也徹底失敗,那我也死心了。但正如大家所知,我大著膽子提出與我個人有關的這七項質疑後,遇到的報復之大又超過想像。這幾天,大陸文化媒體對著我又做了多少事啊。 Q:你也在《借我一生》中提到:「台灣千萬不能把自己好不容易在災難歲月保存下來的、最值得珍惜的東西丟棄了」,以你多年來對台灣文化界的瞭解及敏銳觀察,你認為台灣最值得珍惜的東西是什麼?
Q:你在上海戲劇學院求學,後來回到母校擔任院長,在《借我一生》書中,你提到不少教育理念。請你談談你當初離開戲劇學院時取捨的心境,及對青年學子的人生期許。
永遠有一種超越任何專業的整體性命題在遠處召喚著每一個人,正是這種召喚,決定著人生的終極價值。我離開專業而遠行,是一個笨辦法,而更值得讚賞的行為應該是既不離開又接受召喚,立足專業,問鼎終極意義。 Q:你一生有三次重要的苦讀,和好幾次關鍵時刻的選擇,你說「真正的人生大選擇,是一種缺少參照座標的自我挑戰,需要特殊的勇氣,」你是如何做到的?
|
| Copyright© 1999~2024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天下文化/小天下/遠見雜誌/30雜誌/《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 讀者服務部電話:(02)26620012 時間:週一∼週五 9:00∼17:00 服務信箱:service@cwgv.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