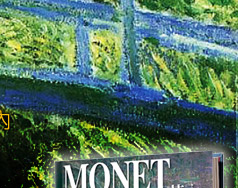印象派的命名者──莫內
要在西洋近代美術史上選一個大眾最熟悉的畫家,可能一定是莫內吧。
因此我也常常在思考:為什麼是莫內?
有什麼原因使莫內的繪畫和大眾有了這麼密切的關係?
在巴黎讀書的時候,常常會一個人,或約三兩朋友,坐火車到奧維(Auver),在梵谷最後長眠的墓地旁靜坐,看他在生命最後兩個月畫的教堂,以及麥田裡飛起的烏鴉。
風景的沉靜荒涼,像是畫家留在空氣中的回聲,還在迴盪呢喃。
我也去過吉凡尼(Giverny)莫內後半生居住與創作的地方,有他親手經營的蓮花池,有他設計的日本式拱橋,有開滿繽紛璀璨花朵的花圃,有他大到嚇人的廚房,牆上掛著一排一排大小不一的銅鍋,比我看過的豪華餐廳的廚具都還要齊全,在擠滿各國遊客的莫內藝術品複製販賣中心(他當年創作的畫室)看到「莫內食譜」,圖文並茂,紀錄藉燒當年莫內招待賓客調製的餐餚料理,令人嘆為觀止。
如果梵谷是藝術創作世界孤獨、痛苦、絕望的典型;莫內恰好相反,他的世界明亮、溫暖、洋溢流動著著幸福愉悅的光采。
因為這樣的原因使我更偏執地願意陪伴在梵谷身旁嗎?
也因為這樣的原因使大眾更熱烈地擁護莫內嗎?
在書寫完「破解梵谷」之後,趨勢基金會的朋友做了一次民調,發函給讀者,詢問下一本希望被「破解」的畫家,結果當然是莫內,他的擁護票數高高超過其他畫家。
感謝這樣的民調,我開始詢問自己:為什麼遲遲不肯動筆寫莫內?
2010的初夏,我開始動筆了,開始破解莫內,也同時破解我自己。
以上是動筆寫「破解莫內」以前先寫好的一篇短序。如今書寫完了,覺得「破解」的功課作完,可以再一次回頭去省視莫內被如此多大眾喜愛的原因,再多說一點話。
莫內是華麗的,他的作品一生追求燦爛華美的光。他的畫裡很少黯淡的顏色,很少用黑,很少用灰,很少用深重的顏色。
莫內常常帶領我們的視覺走在風和日麗的天空下,經歷微風吹拂,經歷陽光在皮膚上的溫暖,經歷一種空氣裡的芳香。
在莫內的世界裡,沒有單純的顏色,他的顏色都是一種光。
因為光,所有的色彩都浮泛著一種瞬息萬變的明度。我們稱做為「色溫」──是色彩的溫度。
然而,色彩真的有溫度嗎。
如果閉起眼睛,用手去觸摸,可以依靠觸覺感知紅的熱,藍的涼冷,可以感知綠的介於冷色與暖色之間的複雜溫度嗎?
創立印象派的莫內相信色彩是有溫度的,因為光緊緊依附著顏色,光滲透在顏色裡,光成為色彩的肉體,光成為色彩的血液,光成為色彩的呼吸,因此色彩有了溫度,色彩也才有了魂魄。
光是色彩的魂魄。
1872年,在破曉前,莫內把畫架立在河岸邊,他等待著黎明,等待第一線日出的光,像一隻黃金的箭,一霎那間,在河面上拉出一條長長的光。
光這麼閃爍,這麼不確定,這麼短暫,一瞬間就消失幻滅,莫內凝視著光,畫出歷史上劃時代的作品「日出印象」。
1874年「日出印象」參加法國官方沙龍的競賽,保守的學院評審看不懂這張畫,學院評審長期在昏暗的、閉鎖的、狹窄的畫室裡,他們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光如此華麗燦爛,如此瞬息萬變。
莫內的「日出印象」落選了。那一年莫內三十四歲,他從十五歲左右就愛上繪畫,從漫畫開始,到十六歲認識了畫戶外海洋天空風景的布丹(BOUDIN),開始走向自然,走向光,走向無邊無際遼闊豐富的光的世界。
莫內會為一次比賽的「落選」失去對光的信仰嗎?
當然不會,莫內自己跟幾個一起落選的朋友舉辦了「落選展」,陳列出他們的作品,希望巴黎的大眾可以來看,可以比較「落選」與「入選」的作品。
「入選」的作品都是古代的回憶懷舊,一個假想出來的不真實的世界。然而,「落選」的作品充滿了當時巴黎現實的生活。火車通車已經有四十年,工業革命改變了一個城市的面貌,市民階層乘坐火車到郊外度假,看著一片一片的陽光從車窗外閃爍而過,他們的視覺經歷著前所未有的亢奮,速度、節奏都在改變,視覺也在改變。
像台北有了最早通蘭陽平原的火車,火車穿行過一段一段隧道,感覺到工業節奏的人們就唱起了輕快愉悅的「丟丟銅仔」那樣活潑帶著新時代精神的快樂歌謠。
莫內的「日出印象」是工業革命對光、對速度、對瞬間之美最早的禮讚。
「日出印象」展出,大眾看懂了,知道這是他們時代的頌歌。然而媒體記者看不懂,自大與偏見使他們活在過去狹窄的框框裡,無法自由思考。
一名自大的媒體記者大篇幅嘲諷莫內,故意引用他畫的名字中「印象」兩個字,批評莫內只會畫「印象」。惡意的嘲諷竟然變成大眾爭相討論的話題,支持莫內,和莫內站在同一陣線的藝術家們因此大聲宣稱:是的,我們就是「印象派」!
莫內的一張畫誕生了一個畫派,莫內的一張畫為歷史上一個最重要的畫派命名,現在收藏在巴黎瑪摩丹美術館的「日出印象」是歷史上劃時代的標誌,莫內是歷史的命名者。
因為莫內的「日出印象」,印象派1874年誕生了。印象派是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畫派,印象派之前,歐洲的繪畫流派大部分侷限在歐美的影響範圍。印象派很快成為世界性的畫派,十九世紀末的台灣,就已經透過日本的引介,接觸到印象派,台灣早期活躍於日據時代的畫家也多半從印象派入手,追求光,追求戶外寫生,追求在不同季節、不同晨昏,對同一處風景的長期觀察。
莫內從巴黎做火車沿著塞納河河港城市寫生,他在哈佛港和塞納河口的阿讓特港(Argenteuil)長達近十年的寫生,在船屋畫室居住畫畫,貼近水面,更細微地觀察水的反光,記錄下光在瞬息間的變幻,這些經驗也都印證在台灣早期畫家坐火車到淡水畫畫,淡水也是河港市鎮,也可以觀察日落的水面反光。
印象派不只影響畫家創作,甚至也影響到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乘坐火車,到河口海濱度假,與家人朋友三三兩兩在風和日麗的季節在公園野餐,享受周休假日的悠閒,這些最早在莫內畫裡看到的現代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已經具體透過政治開明、經濟富裕的結果,成為全世界性的生活現實,成為人們對生活美好的共同嚮往。
因此大眾喜愛莫內,因為那畫中的生活正是他們的生活,貼近他們的嚮往,貼近他們對生活的理解與盼望。
富裕、悠閒、自由、輕鬆,莫內的畫擺脫了傳統歐洲學院傳統的沉重與壓力,傳統的繪畫總是在誇張生命的激情,重複訴說歷史或社會悲劇,而莫內希望把現代人從歷史暗鬱嚴肅的魔咒中解脫出來。
風和日麗,雲淡風輕,春暖花開,一個自由解放的時代,一個沒有恐懼,沒有太大憂傷痛苦的時代,一個放下現實焦慮的時代。莫內帶領他的觀眾走向自然,感覺陽光,感覺風,感覺雲的漂浮,感覺水波盪漾,感覺光在教堂上一點一點的移動,感覺愛人身上的光,感覺田野中麥草的光,感覺每一朵綻放的睡蓮花瓣上的光;感覺無所不在的光,原來,光就是生命本身,光一但消逝,就沒有色彩,也沒有了生命。
莫內的美學是光的信仰,也是生命的信仰。
寫著莫內,寫到1879年9月2日,他站在病床前凝視著臨終的妻子卡蜜兒,這個十八歲跟她生活在一起的女子,他在1865年以後的畫裡畫的都是卡蜜兒,坐著、站著、沉思著,或行動著的卡蜜兒,倘佯在陽光裡的卡蜜兒,在窗邊幽微光線裡為孩子縫補衣物的卡蜜兒,知道罹患絕症的卡蜜兒,撐著洋傘,站在亮麗的陽光裡,一身素白,衣裙紗巾都被風飛起,像要一霎那在風裡光裡消逝幻滅而去的卡蜜兒,如今,她的肉體受苦,消瘦萎縮,在一層一層床單包裹下,卡蜜兒臉上的光在改變,紅粉的光轉變成暗淡紫色,轉變成青綠,轉變稱灰藍,光越來越弱,莫內凝視著那光,他拿出畫筆,快速紀錄著,像迫不及待想挽留什麼,然而,什麼也留不住,卡蜜兒臉上的光完全消失了,完全靜止了,不再流動,只有莫內手中的那張畫,懸掛在巴黎的奧塞美術館的牆上,告訴我們莫內最想留住的光。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金剛經的偈語說的也許正是莫內一生的領悟,夢、幻、泡、影、露、電,都只是瞬間逝去的光吧。
莫內長壽,在二十世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經歷他自己因為白內障視覺受傷的痛苦,在完全看不見色彩的狀況裡,依稀有光,有一點點糢糊朦朧的光,莫內在八十歲高齡繼續創作出長達兩百公尺的巨幅「睡蓮」,含苞的、綻放的、凋零枯萎的,都是睡蓮,都是華麗的光。
1926年莫內逝世,他留下的光繼續照亮這個世界。
數十年看莫內的畫,2010年的夏天終於有機緣動筆寫下我對他的致敬。
七月與八月,六十天時間,完全閉關,我在花蓮,書寫莫內,累了,到七星潭海邊看夕陽的光,看沙卡噹溪谷樹隙的光,看大山山頭漂浮的雲的光,看水面上潾潾波光,看一瞬間飛起的山雀羽毛上的光,看雨後天空的彩虹之光,看盛放薑花一瓣一瓣打開的溫潤如玉色的光,一切都在逝去,但一切也都如此美麗。
我和眾人一樣可以如此深愛莫內,覺得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