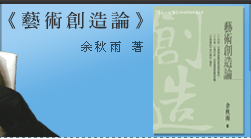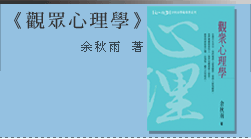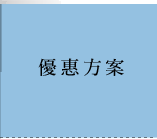| 人生意識
對於情節性的作品來說,「人類生態」的具體形式,就是一個一個的人生。
人生,這個最普通不過的概念之所以要在藝術創造論中鄭重推出,是因為大多數藝術家雖然不能表現人生,卻總是只把它放在背景地位或次要地位上,造成普遍的本末倒置。
有人會說:這無非是在重申藝術要表現人。是的,但又不盡然。我們在這裡不是一般地談論人,而是在強調人生。
人生,是人的歷史性展開,是人的動態發展流程;人生,是人創造自身價值的過程,離開了這個過程,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人;人生,是人自我選擇的長鏈,離開了這條長鏈,便沒有人的存在,更沒有人的本質;人生,是人在客觀世界中的履歷,人因有這個履歷而使自己具備了真實性;人生,是人的生命的具體實現,離開了人生而可以被獨立談論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也有研究價值,卻很難成為藝術表現的主要對象。
在過去受機械唯物史觀的影響只重視客觀題材不重視人的情況下,強調「文學是人學」,呼籲各種藝術對人的皈依,當然是重要的,但在藝術中,人總是呈現為一種感性展開狀態。因此,藝術中的人,大多是人生化的。
與培根「藝術是人與自然相乘」的定義相比,「文學是人學」的說法只說了一半。「人」的「自然過程」,就是人生。
我發現,要說明這個簡單的道理很不容易。多數文學評論者還執著於單向的「人學」,都習慣於對作品的人物性格做靜態解剖,結果從理論到創作,人物的性格概念遠遠強於人生概念。這種狀態,很難適應歷史轉型期的生活現實和創作現實。
其實,時間過程比靜態結構更為重要。如果說某個典型人物可以解析成一個有機組合的系統,那麼,這個系統的來龍去脈是不能被斬斷的。它在不斷地自我調節著,甚至不斷地破損和修復著。阿Q的性格系統已有學者做過細緻的解剖,但我們需要記住的是,魯迅並不是預先精確地設定了這個性格系統再進行寫作的,而是把這麼一個人投放到社會歷史之中,讓他走完他的人生歷程,然後才完成對他的生存本質的確定。在文藝史上,一切寫成功了的人物形象,雖然都有被靜態解析的可能,但總是更明顯地體現了藝術家的過程意識,亦即人生意識。
即便是不直接呈現過程的造型藝術,也總是以瞬間來展示嚮往、憧憬和回憶,總是包蘊著時間上的趨向感,總是溶解著人生意識。即以達文西(插入圖03.1,占2/3頁)的「蒙娜麗莎」(插入圖03.2,占1頁)來說,人們當然可以靜態地解析她的比例、膚色、豐韻、衣衫、髮式、姿態、背景,但是,她的更為吸引人的魅力,在於她的神祕的微笑的由來和趨向。大而言之,她的魅力,在於她正處在自己重要的人生過程和歷史過程之中。同樣,中國古代繪畫中無論是蕭瑟的荒江、叢山中的行旅,還是春光中的飛鳥、危崖上的雄鷹,只要是傳世佳品,都會包藏著深厚的人生意識。
現代不少藝術家已開始從熱衷於描寫性格及由性格衍生的行動,轉變為喜歡描寫行為。行動常常是特定性格的必然結果,而行為則不同,可以有性格的因素,但更決定於人物的社會角色、年齡層次、地域風貌、現實境遇,因而,它對性格的反鑄力大於性格對它的制約力。
在這種轉變中,沙特存在主義的影響不可低估。其實就世界文壇而論,在沙特之前就開始了這種轉變。
沙特不同意種種先驗的決定論,主張從人的各種自我選擇中,從人的行為系列來考察人的存在情況。然後再來裁定人的本質。這種觀念,體現了一種與變幻無常的現代節奏相適應的人生意識,在我看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最值得重視的精神建樹。當然,這種精神建樹也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藝術思維,特別是有關藝術中的人的思維。
其實,比沙特長一輩的法國學者型作家安.莫洛亞已經在《傳記是藝術作品》中指出:
也許,我們比古代的傳記作家感到更迫切需要遵循時間的順序,因為我們不像他們那樣相信存在著永恆不變的性格。我們認為人的精神世界和種族一樣是不斷演變的。我們認為,性格是在與人和事件的接觸中慢慢形成的。在我們看來,在主人公一生的任何時刻都和他相符合的性格是一種抽象的結構,而不是現實。
做為雨果、巴爾扎克、伏爾泰、喬治.桑、普魯斯特的傳記作者,莫洛亞正確地把性格常變關係與時代的變遷聯繫了起來。在古代,生活具有很大的封閉性和自足性,各人所擔負的社會角色,遠不如▲現代生活就不同了,社會生活的無限展示和快速變易,使各個人所擔當的社會角色也處於無窮無盡的波動、更替之中,包括性格在內的人的整體精神狀態,也不可能長久處於自我封閉的穩定方式內。即便穩定,也與變化了的現實構成了不同的比照關係,其實是一種更深刻的變異。為此,現代藝術中這樣的人物已經越來越少:他們到文藝作品中來之前,好像已經活過好幾輩子,他們的性格牌號與他們的社會本質一起,不知在什麼時候早已緊緊地套在他們的頸項下面。他們的出現,只是拼著自己的性格,與別種性格產生對峙和衝突,或者,像變古彩戲法一般,把自己的性格一層層地當眾抖摟出來。
這種貌似穩定的性格構造,對於現代人而言,不僅是不可取的,而且是不真實的。
在美學上,人需要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他自身。如果沒有一個被創造出來而稱之為「人生」的流動的時空世界,就不可能產生這種觀照。因此,人生意識,是審美意識中最基本的內容。
許多藝術實踐家自覺不自覺地體會到了這一點。列夫.托爾斯泰,還有其他難以計數的藝術家都一再宣稱,藝術,表現著對於人生意義的了解。這種主張當然也會受到曲解和攻擊,一九五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弗.莫里亞克曾這樣回答過一種曲解:
「您從來不寫人民。」民粹黨黨員責備我說。
可為什麼要強迫自己去描寫幾乎不了解的階層呢?實際上,無論把什麼樣的人:女公爵、女資產者或沿街叫賣青菜的女販,搬上舞台,幾乎沒有什麼意義,主要是要了解人生的真諦。
《小說家及其筆下的人物》
藝術成就本身,早已證明了列夫.托爾斯泰和弗.莫里亞克的主張的正確。
與老一代藝術家相比,現代藝術家空前強化的人生意識,使他們在藝術上做出了一系列更加引人注目的追求。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隨手舉出一些例子。
一、人生況味
現代藝術家一方面努力把作品中的人和事納入人生的軌道;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他們又從這些人事中超越而出,樂於在總體上品嘗一下人生況味。
不再是分頭表現某個人命運悲慘,某件事結局淒苦,不再是遠遠地欣賞英雄豪氣或兒女柔情,不再是謹慎地劃分人性的光明和黑暗面。在現代藝術家看來,每一個人在自己的人生履歷中都會與這些不同的滋味相遇,它們全都來自人生。人生的險峻在此,人生的美好也在此,人生的無常在此,人生的魅力也在此。正因為人人都有可能遭遇,因此這是藝術家把欣賞者拉入共同體驗的聰明手段。
有的作品,讓我們品嘗了人生的苦澀之味,又立即告訴我們,這在所有的人生中都無可逃遁。這不是人生的偏門,而是人生的本味。
有這樣一部現代外國電影,女主人公的丈夫因酗酒鬧事,進了監獄,她一人在鄉間撐持著家庭。一位獨身的中年醫生來到鄉間休假,天天在湖上看到女主人公沉靜蘊藉的綽約風姿。女主人公當然也發現了醫生,這位無論在哪一方面都遠遠超越了自己丈夫的男人,而且顯而易見,他正愛著自己。但是,他們無法再進一步靠近,霧的湖上,一次次交叉著他們搖船的身影,但兩人都默默無聲。他們的障礙是,女主人公的丈夫在監獄裡。這在別人看來可能是一個離婚的理由,但在受到起碼道德制約的女主人公和醫生看來,這倒成了他們不能進一步接近的原因。他們誰也不想成為投井下石、雪上加霜之人。更何況,女主人公還撐持著一個家庭,她一旦離去,更大的悲劇將會發生。於是,他們終於在悵惘和遺憾中分手。哀怨苦澀的情緒,恰似畫面上始終不散的濃霧。
若就題材而論,這裡裹藏著許多常人不一定會遇到的偶然因素,如丈夫入獄、醫生渡假之類;但是,藝術家絕不是要我們僅僅去客觀地觀看一個罪犯的妻子的苦惱,或一位休假醫生在愛情上的煩悶。他所渲染的苦澀帶有人生的整體性:人啊,在能夠愛、有權利愛的時候,總是太年輕、太草率,他們的閱歷太淺,他們選擇的範圍太小,他們遇到異性的時機太少,因此,初戀初婚常常是不幸的,儘管人們的自尊心和適應力很快就掩蓋了這種不幸。當然,他們終於會跨入能夠清醒選擇的年歲,可惜在這個年歲他們大多已失去了選擇的權利。他們的肩上已負荷著道德的重擔,他們的身後已有家庭的拖累,他們只能面對著「最佳選擇」,喟然一嘆,匆匆離去。
人生,有沒有可能從根本上擺脫這種苦澀而尷尬的境況呢?似乎很難。即使是在遙遠的將來,在更趨健全的人們中間,舉世祝福的青年戀人仍然會是草率的,而善於選擇的中年人仍然不會那麼輕鬆地去實現自己的選擇。誰叫人生把年齡次序和婚姻時間排列得如此合理又如此荒誕呢?因此,誰也不要責怪,事情始源於人生本身所包含的吊詭。只要進入人生,就會或多或少地沾染這個吊詭,這個悖論。
顯然,看這樣的作品,如果只是去欣賞某一地區某一類人的生活現實和精神風貌,實在是違背了藝術家們的初衷,也離開了作品本身所傳達的實質性內容。它要讓我們品嘗的是人生的一種整體況味:極有魅力的苦澀。
有的作品,讓我們品嘗了人生中更為常見的一種況味——世態炎涼、人情冷暖。
中國傳統的文藝作品中,頗有一些篇什涉及到這種人生況味,但多數有著更為濃重的道德說教和消極感慨,結果,人生本體被湮埋、被耗損了。這樣的作品流傳於世,人們感動的仍然是它們觸及活生生的人生的部位,但藝術家往往要讓它們依附於一個政治事件,或者歸咎於主人公們的立場品質。這就造成了藝術從未離開人生而又很少專門品味人生的常見局面。對此,現代藝術家漸漸醒悟,他們更願意在人生歷程和人情冷暖上多做一些文章,讓其他背景性內容隨之而轉移,而不要產生本末倒置的現象。
又是一部外國電影。一位社會地位很高的著名音樂家與夫人一起駕車外出,車是夫人在開,不慎撞死了一位老婦。做為丈夫,音樂家很自然地代替夫人承擔了法律責任。他自知要被捕,匆匆逃出幾天,回鄉去與年邁的父親告別。於是,他潛身於人群、蜷曲於車站,潦倒不堪,品嘗了與他以往的生活完全不同的落荒滋味。一個車站食堂的女服務員約略感受到了他與卑微處境不和諧的某些氣質,盡力幫助他。此時,女服務員是他的恩人,但女服務員根本無法想像他幾天前所過的那種高貴生活。這種因一個偶然的觸因而構成的人生起落比照,本來就已經很有意思,藝術家更進一步,讓落難中的丈夫又一次看到了他夫人的面容。夫人是國家電視台的播音員,當然處處可以看到她的面容。令人沮喪的是,她明明知道撞死人的是她自己,丈夫只是代她受過,她明明知道現在丈夫正在法網的邊緣上掩顏奔突,去與老父做最後的道別,但她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面容卻是那樣安詳平適。音樂家凝視著安置在公共場所的電視屏幕,愕然木然。這是他過去的生活、過去的家庭,僅僅幾天時間,一切都變得那樣遙遠。他顫慄了,面對著人生的乖戾。
他很快被判罪,到遙遠的北方去服役了。長久沒有夫人的任何消息。一天,看守警察通知他夫人來訪,當他匆匆趕到指定地點而不見人的時候,憂心忡忡。他疑惑著夫人到來的可能性,而心頭卻有一絲另外的希冀。冒稱「夫人」來訪的,果然是車站邂逅的女服務員。他流淚了,又笑了,他知道,他在人生的絕路上又獲得了新生,而新生的機遇,又來得那麼怪異。第二天早晨,他沒有及時趕到服役地,當「夫人」陪著他走近監獄高牆時兩人早已筋疲力盡。高牆內,罪犯已在列隊、點名,他的遲到,使警察們想到了潛逃的可能。但是,他不會潛逃,也不必潛逃了,尤其在今天。他與他的愛人,累倒在高牆外面,拉起了隨手帶著的一架手風琴。音樂家,又一次以音樂向人生報到。牆內的警察寬慰地笑了,朝陽、晨霧、樂聲,在一個最為人們所不齒的地方迎來了新的人生。
這個作品,沒有像某些不失深刻的作品那樣評判社會等級的差異、揭露法律的不公,也沒有包含對其他社會問題的研究和探討,更沒有讓音樂家做什麼沉痛的懺悔。對於前夫人,作品有所否定,但也沒有流連於此。藝術家根本沒有給這個不知感恩的風雅女人以更多的篇幅,完全不去表現她在丈夫入獄後的生活和考慮。因此,這個作品也沒有注重於道德評判。
傳統的藝術家也許會指責這樣的作品在情節結構上的散逸,你看:明明產生了丈夫與夫人之間的糾葛,這種糾葛產生的後果又極為嚴重,藝術家卻輕輕地、早早地把夫人丟棄了;明明矛盾的起因是一起車禍,但既不表現法庭,又不表現死者家屬;明明案情緊迫,正在緊張審理,卻讓當事人離逸千里返故鄉……然而,這一切不是藝術失誤,而是藝術家的故意追求。作品要表現的就是偶然性因素疊出的人生際遇,故意不關心除人生際遇之外的種種人事糾葛。因此,駕車釀禍之途,成了對音樂家前一段人生道路的了結;隻身返鄉之途,成了他體察人世冷暖炎涼貴賤善惡的岔道;而兩人氣喘吁吁奔向監獄高牆之途,則是一條在險惡中發現晨曦的新的生活道路。路,坐著汽車,坐著大車,邁著雙腿走過的路,最敏感,也最透澈地體現了人生所能感受的溫度。
西方現代不少藝術作品,從品味人生的傷感、寂寞、滅絕,到品味出其中的荒誕意味和滑稽意味。對此,不少受傳統藝術觀念薰陶時間較長的人感到很不習慣。
其實這樣的作品更具有人生的深度。從根本上說,它們是在濃烈地傳達一種作者感受到的人生況味。是人生面不是社會,是況味而不是思想。荒誕派作品中的主角,不是純客觀的觀賞對象,往往包括作者自身;但又絕不僅僅是作者的自我形象,往往包括著觀眾,包括著更廣的人群。簡言之,這些角色,大多是藝術家心目中包括他自身在內的人類總體生態的濃縮,怪異的劇情,則大多是人生過程的象徵。它們以具體微觀的展現方式,與人類生態進行著宏觀聯結。
有些現代藝術也體現了人生的另一類況味:和美、堅毅、報償。美國電影「金池塘」展現了一種極為美好的人生晚年。是誰給了這對老年夫妻以如此富有魅力的晚年歲月?不是他們的女兒,也不是社會福利院,更不是百萬家私、飛來橫財,而是人生本身。漫長的人生,使他們之間的關係已完全調適,調適到了天然和諧的地步。悠遠的歲月,使他們世俗的火氣全消,只剩下了人生中最晶瑩的精髓。終點的臨近,使他們再也無意於浮囂的追求,更珍惜彼此的深情。於是,毫無疑問,最美好的饋贈,正是來自人生。
二、人生命題
在人生問題上,現代藝術家所跨越的步子,遠不止上面這樣的例子。上面這樣的例子,也能容易見之於優秀的傳統藝術家,他們更大膽的追求在於:把一系列很難人生化的課題也一一人生化了。
也就是說,現代藝術家的人生意識,對一系列非人生化的理念、歷史、自然,以至政治、軍事、經濟等等,全都做出人生化的處理。
最有說服力的例子也許是兩個橫隔二千多年的同名劇本的比較。
公元前四百餘年的古希臘作家索福克勒斯(插入圖03.4,占1/4頁)創作過一個著名悲劇《安提戈涅》,二千三百八十多年之後,法國現代作家讓.阿努伊於一九四四年重寫了這個劇本,基本故事沒有太大改動,但人生意識卻大為加強了。
這兩者之間的對比有點深奧,因此必須先把故事交代一下。
這個故事的大體情節是:
國王克瑞翁宣布安提戈涅小姐已死的哥哥有叛國罪,不准下葬,安提戈涅要埋葬哥哥而被捕,並被判死刑。但安提戈涅正恰是國王兒子的未婚妻,國王正想免去安提戈涅死刑時,安已在囚室中上吊自盡。國王兒子隨之自盡,國王妻子也因失去兒子而自盡。國王對著一具具屍體,後悔而茫然。
這齣戲,表現了兩種自成理由的理念的衝突:國王代表著國家的倫理力量和法律觀念,安提戈涅則代表著另一種更為宏大的倫理力量,堅信兄妹手足之情的合理性,否定曝屍不葬的指令有違天下情理。這場衝突,也可說成是「王法」與「神律」的對立。在黑格爾看來,兩方都有理由,又都有片面性。衝突使兩方的片面性遭到了挑戰和否定,以各自的毀滅呼喚著一種永恆的正義。
這個故事到了二十世紀歐洲藝術家手中就出現了另一種精神內涵。讓.阿努伊把「王法」和「神律」兩種理念的衝突改寫成兩種人生哲學的對峙,而且又讓這兩種人生哲學歸屬於兩個不同的人生階段,這樣,這場衝突就徹底地人生化了。
國王克瑞翁成了隨波逐流的人生哲學的代表者。他本來也愛好藝術和學問,並不追慕權勢,由於一個特殊的客觀原因,他不得已而成了國王。既然做了,總得像其他國王一樣執法,儘管他本人並不想找事,也知道執法中有許多不光彩的事。他不是暴君,也不是明主,位居至尊而沒有個人意志。他被動得像動物,而不會像人一樣主動地來選擇行動。他深知自己在處罰安提戈涅這件事上,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而被處罰的安提戈涅卻很光彩。因此,他坦率地向安提戈涅述說了自己的苦惱,要安提戈涅不要與他過不去,使他更不光彩。他反複地勸說安提戈涅結婚、生孩子,做一個與大家都一樣的女人。
安提戈涅則被現代藝術家處理成了敢做敢為、敢於掌握自己命運的那種人生哲學的代表▲。她的目標十分明確,即要以自由意志來戰勝權勢。她在哥哥下葬的問題上挺身而出,倒不是出於兄妹之情,而是覺得國王在玩弄權勢,她要鬥爭到底。她不怕選擇死,是因為她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是自由意志的捍衛者。她與國王的辯論,不是圍繞著具體事件本身,而是圍繞著兩種人生哲學展開的。
現代藝術家還不滿足於兩種人生哲學的對照,而還想進一步,認為任何重要的人生哲學都有可能出現在同一個人生中。為了把國王與安提戈涅的兩種人生哲學,統一在同一個人生系列上,現代藝術家又進一步別出心裁,故意在年齡層次上拉開距離並加以強調。他讓安提戈涅這一角色變得兒童化,纖弱瘦小,處處保留著童年的習慣,天沒亮就蓬頭散髮地跑到花園裡去玩了,她帶著童心愛撫小狗,準備赴死時只托別人照顧好小狗。她無所畏懼,但她還向乳母撒嬌,在去埋葬哥哥屍體時用的還是一把兒童的小鏟子。與她相對比,國王克瑞翁卻是一種成年人的典型,成年與兒童的根本區別就是學會了妥協。國王自己也深知成年人的悲哀,因此對自己的小侍從說:「小傢伙,永遠別長大!」
至此,劇作不僅把兩種社會理念變成了兩種人生哲學,而且又把它們做了一體化處理,讓世人領悟:每個人都會經歷這兩種年齡階段,因此,每個人,都會有敢做敢為的安提戈涅的時代,也都會走入妥協被動的國王的時代。在讓.阿努伊筆下,國王和安提戈涅的地位和身分是無關重要的,他力求讓他們平凡化、普遍化,變得與各種人都很親近,都可互相感受。結果,古希臘的這齣著名悲劇,在二十世紀便成了一個探討人生底蘊的作品。
從這個戲也可看出,現代藝術家要把漫長、複雜的人生融於一個作品中予以研磨,就不能不採用一些有特殊概括力的怪誕手法。要讓這種研磨通過直觀感性的形象體現出來,怪誕手法又可升格到整體象徵的地步。
歷史,也可獲得人生化的處理,從而使人類整體和個體互包互孕。人類的整體史與個體生命史有著深刻的對應關係,個體生命史是可以體察的,因此,一旦把歷史做人生化處理,它也就變得生氣勃勃,易於為人們所體察了。把歷史看得如同人生,這在人生觀和歷史觀兩方面來說都是超逸的,藝術化的。
本文摘自《藝術創造論》第三章 人生意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