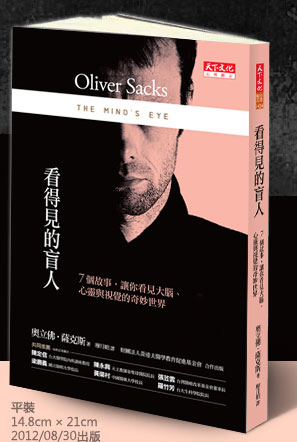臉盲
即使我和一個人五分鐘前才見過面,
只要換了一個地方,又不認得人家了。
例如有一個早上,我才跟我的精神科醫師會談過。
我離開診間,幾分鐘後,
看到一個穿著樸素的先生,在醫院大廳跟我打招呼。
我不知道這個陌生人是誰,後來,警衛跟他打招呼,
我才恍然大悟:他就是我的精神科醫師。
打從出生那一刻,到死亡為止,我們都以自己的臉孔面對這個世界。我們的年紀和性別都顯現在臉上。我們的情感,不管是達爾文曾探討的公開、本能的情感或是佛洛依德研究的潛藏或壓抑的情感,還有我們的思想和意圖,都會顯現在臉上。
雖然,我們會欣賞美麗的手臂、腿、乳房和臀部,但從審美的觀點來看,我們判別美醜總是看臉;評斷一個人是否善良、聰不聰明,也都是看那人的臉。更重要的是,正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張不同的臉,才能區隔出獨立的個體。我們的臉上有經驗和性格的印記。有人說,年過四十,就必須為自己的容貌負責。
嬰兒在二個半月大的時候,看到笑臉也會跟著微笑。艾林伍德(Everett
Ellinwood)論道:「嬰兒的微笑會使大人想跟他互動——對著他笑、跟他說話、抱抱他——換言之,亦即嬰兒社會化的歷程就此展開……只有在母嬰雙方繼續不斷以臉對話的情形下,兩者才能互相了解。」心理分析師認為,臉是第一個具有重要視覺意義之物。但就神經系統的角度來看,臉是否在一種特殊的分類當中?
自我有記憶開始,我就發覺自己常常無法辨識臉孔。我小時候並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中,但是在我長成青少年、進入新學校就讀的時候,這個缺陷就常讓我感到困窘。我即使看到老師,也無法分辨他們誰是誰,老師不僅覺得奇怪,有時甚至為此惱怒。他們完全沒想到我有知覺障礙(話說回來,他們怎麼會曉得?)。我倒是能認得來往密切的朋友,特別是最要好的兩個:艾瑞克和強納森。但這是由於他們有明顯的特徵,讓我容易辨認:艾瑞克有著一雙濃眉,戴著鏡片厚厚的眼鏡,而強納森高高瘦瘦,有一頭亂得像拖把的紅髮。強納森善於觀察別人的姿態、手勢和臉部表情,不管看到任何人的臉龐,似乎都過目不忘。十年後,我們一起看老同學的照片,他還能認出幾百個同學,我則連一個都認不出來。
我不只拙於認人。我去散步或騎腳踏車總是走同一條路。因為我只要稍稍偏離原來那條路,絕對馬上迷失方向。如果我想去騎車探險或是去沒去過的地方,那就非找個伴不可。
我今年已七十六歲,儘管這輩子都在努力補償無法辨識臉孔和地方的缺陷,但似乎一直沒什麼改善。即使我和一個人五分鐘前才見過面,只要換了一個地方,又不認得人家了。例如有一個早上,我才跟我的精神科醫師會談過(過去幾年,每週兩次,我都準時到這個醫師的門診報到)。我離開診間,幾分鐘後,我看到一個穿著樸素的先生,在醫院大廳跟我打招呼。我不知道這個陌生人是誰,但他似乎認得我。後來,警衛跟他打招呼,我才恍然大悟:他就是我的精神科醫師。(在下一次門診會談的時候,我提起這件事。我認為這是神經方面的問題,而非精神障礙,但他似乎不完全相信我說的。)
(更多詳細內容請見《看得見的盲人》)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