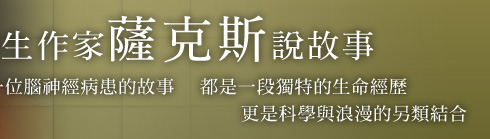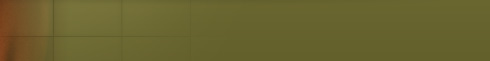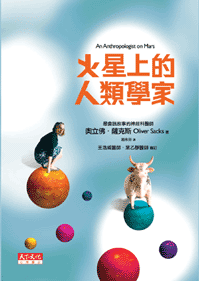|
第一章 失去色彩的畫家
一九八六年三月初,我接到這樣一封信:
我剛過六十五歲,是個頗成功的畫家。今年一月二日,我開車出去,被一輛小卡車撞到我車子的右側。我來到當地一家醫院的急診室,當時醫生告訴我說,我有腦震盪。在做眼部檢查的時候,發現我無法分辨出字母與顏色。那些字母看來就像希臘文字。我看每樣東西的感覺,就像在看黑白電視螢幕一樣。過了幾天,我認出字母來了,我的視覺變得跟老鷹一樣,能把一條街以外一隻扭動的蟲看得清清楚楚,視力簡直銳利無比。然而,我竟是徹底的色盲。
我去看過許多眼科專家,他們對這種色盲病情毫不了解。我求診於神經科醫生,也是無功而返;催眠中的我仍然分辨不出顏色,我曾做過各式各樣的測驗,隨便你說個名稱,我都做過。我那隻棕色的狗變成暗灰色,蕃茄汁是黑色,彩色電視成了一堆亂糟糟的東西……。
此人又繼續寫著,問我以前有沒有遭遇過這種問題;我能不能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還有我能不能幫他?
這似乎是一封驚人的信。一般人所知的色盲,都是天生的,像是無法分辨紅色、綠色或是其他顏色,或是由於視網膜反應色彩的錐細胞有缺陷,以致於完全看不出任何顏色,不過這種情形極為罕見。但是,顯然這位寫信來的艾先生情況絕非如此。他一輩子都很正常,打從出生以來,視網膜內的錐細胞就很完整。在視力正常了六十五年之後,他卻變成徹底的色盲,彷彿「看黑白電視螢幕」似的。事出突然,跟視網膜錐細胞可能發生的緩慢退化互相矛盾,卻反而顯示出,有更複雜的病情發生在腦部專司色彩知覺的部分。
完全色盲
儘管在三世紀以前,即曾有文章描述腦部受損引起的完全色盲,其現象卻極罕見,.也十分重要。它一直令神經學專家感到好奇,因為正如所有神經的瓦解與毀滅一般,完全色盲使我們得以一窺神經構造的機制--具體來說,也就是頭腦如何去「看」或是製造色彩。徹底色盲發生在一名畫家身上,更令人加倍好奇。對畫家而言,色彩是最重要的,他可以直接畫出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因而將其奇特的病痛,其實傳達出來。
色彩並非小事,而是數百年以來,藝術家、哲學家與自然科學家無比好奇的焦點。青年時代的史賓諾莎第一篇論文,就是以彩虹為題;牛頓年輕時最令他雀躍的,即是發現白色光的組合成分;歌德偉大的色彩研究也如同牛頓的發現一般,始於一片三稜鏡;十九世紀的叔本華、楊格、赫爾姆霍茲與馬克士威,都受到色彩問題的魅惑,而維根斯坦最後一篇作品,即是他的《色彩論》。可是大部分的人十之八九的時間,卻忽略了色彩的大秘密。從艾先生的個案中,我們不僅可以探索並不明顯的大腦機制或是生理學,更能研究色彩現象學,以及色彩對個人共鳴的深度與意義又是如何。
接到艾先生的來信之後,我和好友兼同事華瑟曼連絡,這位眼科專家認為,我們需要一起深入研究艾先生的複雜病情,可能的話,也必須儘量幫助他。我們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和他第一次見面,他身長而削瘦,有一張精明、聰慧的臉孔。儘管他因為病情的關係而神色沮喪,態度卻很快熱絡起來,開始生動又幽默地與我們交談著。他說話時一逕抽著菸,不安的手指上沾有尼古丁的污跡。他描述身為一名畫家極為活躍且豐富田的生活,早從他在新墨西哥追隨名畫家歐奇芙中的日子,一九四○年代在好來塢畫布景,一百到五○年代在紐約成為抽象派風格畫家,以及後來擔任藝術指導,以及商業畫家的經歷。
被遺忘的車禍
我們得知他的意外也伴隨了短暫的失憶症。在車禍發生當時,顯然他還能夠向警方清楚交代發生意外的情形,當時是一月二日的下午;可是,之後由於他頭痛愈來愈厲害,於是回家休息,他對太太抱怨頭疼得很,也覺得迷糊,但對車禍之事竟然隻字未提。後來他陷人一場長長的昏睡。一直到次日上午,他妻子看見車子的側邊凹進去一大塊的時候,才問他怎麼回事。但她問不出個所以然(「我不知道,可能是有人倒車時撞到了。」),這時她曉得一定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
之後,艾先生開車到畫室,發現桌上有一份警方的車禍報告。他出了一場車禍,但奇怪的是,他卻毫無記憶。或許那份報告可以使他恢復記憶,然而拿起報告一看,他卻什麼也看不懂。他看見不同大小的字體,個個清晰無比,但看起來卻像「希臘字母」或是「希伯來文」。即使用放大鏡看也沒用,只是讓「希臘字母」或「希伯來文」變大一些罷了(這種無法讀字的失讀症持續了五天,後來就消失了)。
艾先生這會兒認為他一定是得了腦中風,或是因為車禍而腦部受損了,於是他打電話給醫生,後者為他安排到當地醫院做檢查。正如他第一封信中所說的,雖然此時已檢查出他無法辨別色彩,也不會認字,但他一直到次日,才知覺到眼前的色彩已完全改變。
當天他決定到畫室工作。他明明知道那是一個陽光普照的早晨,但卻覺得自己竟彷彿在霧裡開車似的。每樣東西似乎都霧茫茫的,變成白色、灰色、一片模糊。快開到畫室的時候,他被警察打手勢攔住車,他們說他闖過兩個紅燈,問他知不知道?他說他不曉得,不知道自己闖了兩個紅燈。他們發現他並沒有酒醉,而且顯得一臉困惑與病容,於是給他一張罰單,並且建議他求醫。
艾先生終於來到畫室時,心中鬆了一口氣,以為那一片可怕的霧會就此消失,一切又會清楚起來。可是他一跨進門,發現原來掛滿了色彩繽紛圖畫的畫室,如今卻成了徹底的灰色,或是完全沒有色彩。他向來以繪畫抽象色彩著名,這會兒的畫布,居然是灰灰、白白或是黑色的。他的畫--曾經充滿了聯想、感情與意義--如今看來,竟是那麼的陌生,而且沒有任何意義。直到這一刻,一股莫大的失落感向他襲捲而來。他這一生都是個畫家,而今連他的藝術也變得毫無意義,他簡直不能想像日子該如何過下去。
往後的幾個星期變得非常難過。「你可能以為沒有色彩的感覺,又有什麼大不了?」艾先生說。「我的一些朋友就這麼說,我太太偶爾也這麼想。但是,至少對我而言,這實在是太可怕,也太令人作嘔。」他明白每樣束西的顏色為何,而且知道得十分確切(他不但能說出每種色彩的名字,更能一一指出各種色彩在色卡上的編號,因為他已使用這種色卡多年)。他可以毫不猶豫地辨認出梵谷撞球桌的綠色,用的是哪一號的綠色調。他對最偏愛的每幅圖畫所用的每一種色彩都十分清楚,但現在他再也看不見這些顏色,即使用心靈的眼睛去看,也看不到了。現在也許他只能靠言語上的記憶,才知道什麼是色彩。
他失去的不僅是色彩,出現在他眼中的一切,都是可厭的「骯髒」模樣;白色刺眼,有些褪色的感覺,而且不是很乾淨的白色;黑色也是濁濁的--一切都不對,不自然、髒兮兮、不純淨。
灰色世界
艾先生也幾乎無法忍受人們變了樣的長相(彷彿會動的灰色雕像),更受不了自己在鏡中的影像;他迴避社交活動,性交更是不可能。他看見人們的肉、妻子的肉,以及他自己的皮肉,都是令人嫌惡的灰色;對他來說,「肉色」如今看來成了「老鼠色」,即使他閉上眼睛也是如此,因為他逼真的視覺心像雖然保留下來,但卻喪失了顏色。
一切都「不對」不但令人困擾,更叫人厭惡,而且日常生活中每種事物皆是如此。他發覺食物令人作嘔,因為每樣食物看來都灰灰的、死死的,他必須閉上眼睛才吃得下去。但這也沒多大幫助,因為他心中一顆蕃茄的形象,就像他眼中看見的一樣漆黑。因此,在無法修正心中意象的情況之下,他轉而只吃黑色與白色的食物--如黑橄欖與白米,純咖啡與酸乳酪。這些至少看起來比較正常;而大部分正常顏色的食物,看來卻恐怖無比。他家裡那條棕色的狗,如今看來好奇怪,他還真想另外養一隻大麥町算了。
他遭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與痛苦,從紅綠燈號的混亂(現在他只能從燈號位置來辨別紅燈或綠燈),到完全無法選擇衣服(他妻子必須先把衣服挑好,但他對這種倚賴性實在難以忍受,後來他把抽屜與衣櫥裡所有東西分門別類--灰色襪子放這裡,黃色放那兒,領帶寫上標籤,外套與西裝分類,以防他搞混,或是搭配色彩極不調和的衣服一。餐桌上各項物品的位置也必須固定,否則他可能錯把芥茉當成美乃滋;或者他有可能抹上「黑色」的東西,而錯把蕃茄醬當成果醬。
幾個月就這麼過去二,他尤其懷念春天繽紛的色彩--他向來愛花,可是現在他只能從形狀與味道來分辨。藍?鳥不再色彩斑攔;奇怪的是,原本亮麗的藍色,如今看在眼裡,卻成為淡灰色。他再也看不到天空中的白雲,雲的雪白成了他眼中摻雜著灰色的白色,無法從天空的藍色中分離出來,因為藍色似乎褪成淡灰色。紅椒與青椒也完全分辨不出來,但這是由於兩種顏色看來都是黑色。他看黃色與藍色時,則都近乎成為白色。
艾先生似乎也經歷一種極度的色彩對比,他不再能夠分辨出細微的色調差異,在直接日曬與強光下尤其如此;為此他以鈉燈的效果作了個比喻,在鈉燈的照射之下,色彩與色調的微妙差異不復存在,此外有一種特別的黑色膠卷--「如三X速度膠卷」--即可產生一種強烈的對比效果。有時候物體異常突出,就是因為過度的色彩與清晰度,正如側面影像一般。但是如果對比正常,或是稍弱的話,可能就完全看不見了。
因此,儘管他棕色的狗站在光線充足的路上,可以像側面影像一般清晰,但是只要狗兒跑到光線柔和且斑駁的灌木叢中,可能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人的身影在半英里之外,可能仍看得見(正如他在第一封信中所說的,之後他也常常提到,說他的視覺變得愈來愈清晰,「就像老鷹的眼睛一樣銳利」),但是直到人走得非常接近,他才辨認得出臉孔。這似乎是類似喪失對比色彩與對比色調,而非認知方面的缺陷,也就是並非喪失辨識物體的能力。
他開車時,碰到一個大問題,就是他總把陰影錯看成路面的裂縫或凹痕,所以會因為想避開,而突然剎車或轉向。
他覺得彩色電視特別難以忍受:其影像總是令人不悅,有時候完全一片模糊。他覺得黑白電視倒比較容易應付,因為他的視覺對黑白影像的接收比較正常,反而是每次看見彩色影像,總是覺得怪怪的,受不了(我們問他何不關掉顏色時,他說他認為「褪色」的彩色電視的色值,似乎跟「純」黑白電視不同,而且比較「不平常」一。但這會兒他卻解釋說,他的世界並不真的像黑白電視或電影,這點倒跟他第一封信不盡相同--倘若真像黑白電視或電影,日子反而比較好過(他偶爾會好希望能戴上一付小小的電視眼鏡)。
住在鉛鑄的世界
由於他很難讓人了解他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模樣,一般的黑白比喻又沒什麼作用,沮喪之餘,他終於被逼得在數週之後,弄出一個全灰的房間,一個全灰的畫室、灰色的宇宙,其中的桌子、椅子以及一桌子精致的晚餐,全部都畫上不同色調的灰色。習慣於「黑白」的我們,看見各種不同的灰色調滿布於三度空間中,其效果的確恐怖,跟黑白照片完全不同。正如艾先生所說的,我們接受黑白照片或電影,是因為它們是真實世界的代表 我們能夠看到的影像;或是我們不想看的時候,可以遠離的東西。然而對他來說,黑與白都是真真實實的,全面環繞著他,結結實實的三度空間,一天二十四小時存在於他的周遭。他認為唯一表達的方式,即是製造出一個全灰的房間,讓他人親身體驗一番--當然,他說,觀察者自己也必須全身畫成灰色,如此一來,他即成為周圍的一部分,而不僅是觀察而已。更重要的是,觀察者也必須和艾先生一樣,喪失對色彩的知識,他說這就好比住在一個「鉛鑄」的世界似的。
因此,他說「灰色」或「鉛色」都不足以描述他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模樣。他說他看到的不是「灰」色,而是一種一般經驗與普通言語完全無法比擬的視覺特質。
艾先生再也無法去逛美術館或是藝廊,當他看見最喜歡的圖畫的彩色複製品時,更是難以忍受。這不單是因為畫已盡失色彩,而是由於它們看起來「錯得離譜」,充滿了褪色的或是各種「不自然」的灰色調(黑白照片倒是好得多)。如果碰到認識的畫家,更教他心煩意亂了,他們的作品在他眼中的評價降低,使他難以分辨出畫家的身分--而他覺得這正是此刻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