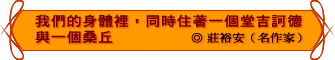
塞萬提斯起先想詆毀騎士小說,因此以輕蔑而滑稽的態度描繪堂吉訶德,沒想到這個角色越來越複雜,彷彿超過作者的掌控。一如福樓拜起先與愛瑪、羅曼史小說的疏離,但小說殺青後,不得不挺身告白,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堂吉訶德早先誤看風車、綿羊、銅盆,讓人哈哈大笑。但是越接近他的內心世界,就越發現堂吉訶德深深相信他「應該看到的」,而不是他「真正看到的」,這是何等高尚的情愫與堅持。到底通過觀看,抑或通過想像,我們會更瞭解真實?我一直非常喜歡,堂吉訶德第三次出遊,突然看到事物的本相,誤以為被下魔咒。這時已能夠欣賞夢幻之境的桑丘,反過來以語言為他虛構畫面,鞏固主人的想像力。這個主僕易位的設計,讓我永遠記得,我們的身體裡,同時住著一個堂吉訶德與一個桑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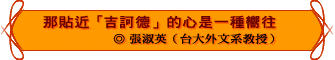
傅柯在《瘋癲與文明》裡提到,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是兩位將「瘋癲」著墨最佳的卓越典範。吉訶德因「瘋癲」流芳百世,他的「瘋癲」卻讓死亡不朽。爾今,「吉訶德」可以侃侃而談:「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呼?」西班牙人說:「初讀《吉訶德》,譏笑;再讀《吉訶德》,深思; 三讀《吉訶德》,流淚。」四個世紀以來,百工各業,多少人曾自詡為「吉訶德」!那貼近「吉訶德」的心是一種嚮往、一種狂狷、一種謙卑、一種自我解嘲(解脫)、一種志業與理想(多麼繁複的理性與感性的糾葛啊!)。但「吉訶德」(塞萬提斯)絕對不是「坐而言」的「完美主義者」。

多少年來,身材不高的堂吉訶德與他的瘦馬、舊盾早已凝結成俗世最浪漫的騎士精神形象,此浪漫也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遊俠騎士的浪漫於今是一種巨大失落的過時品質,這種品質像午夜夢迴不斷搗進我們夢田的執拗靈光,靈光消失年代,浪漫主義者的奢華是藉著重返堂吉訶德千變萬化的形形色色旅程世界來得到撫慰,從而感到「斯人有斯疾」的失落傷懷,與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惆悵與理解。
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既荒謬又真實,時發議論與多管閒事的雞婆,也許現今看來他是個帶著過度自以為是的傻子精神,但能夠像吉訶德先生瘋癲得這樣有條不紊的人也實在是稀有的,隨著吉訶德的長征歷險,我們也跟著走上漫遊奇想旅程,在旅途裡,餐風露宿為了冒險,而冒險是為了心中不止息的浪漫情愫,堂吉訶德可說是解放了被體制與物質世界緊緊束縛住的我們。
這個時代我們需要更多的「堂吉訶德」。